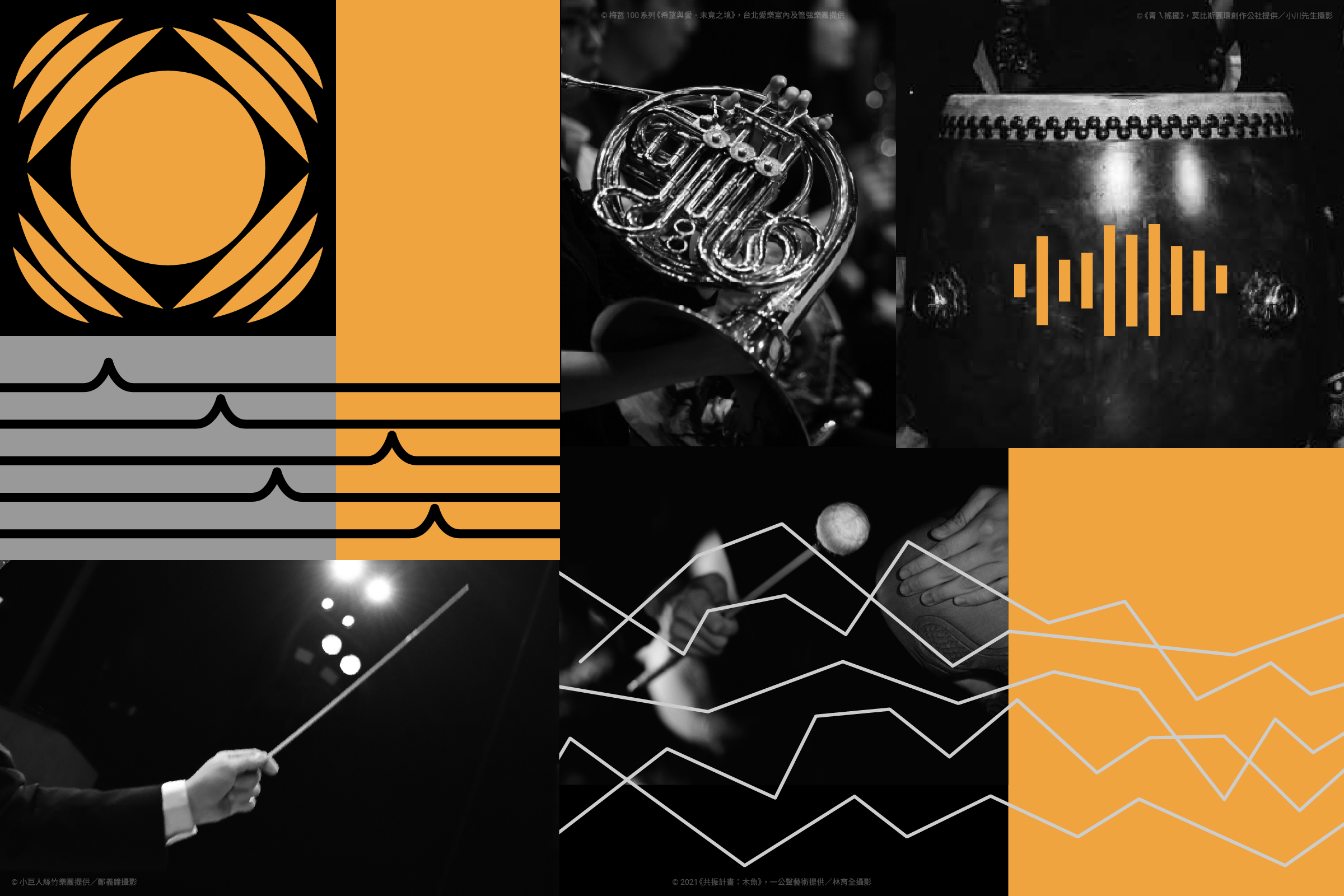
文 蔡孟凱(2025年度專案評論人)
先從音樂會的標題談起吧。
無界的疆域,聽起來浪漫卻無疑是句矛盾語。「疆」字義本身便是界線、邊界的意思,要想像一片疆域,必然會有一條因應而生的界線,用以區分裡外、同異、你我。這條線可以是明確而有形的蕃界、隘勇線、或是傳統領域,但更多時候是只存在於思想之中,人類本能拒絕他者的分別心。藉由疆域,人們劃出一塊同時具備物質和精神意義的舒適圈,一塊毫無罣礙自在遊走的區域,這樣的概念如何得以無界?
《無界的疆域》在英文譯名又額外提出三個命題:土地、信仰、記憶(Songs of Land, Faith, and Memory)。土地,財富與資源的基礎,全世界原住民族至今仍在奮鬥追討的資產;信仰,人類得以在宇宙中定義自身的倚靠,一把同時可以促成和解或仇恨的雙面刃;記憶,最可靠又最不可靠的時間印記,傳承歷史的終極手段,卻可以輕易地被抹消噤聲。在客觀的地理位面和歷史長河之中,這三個概念都曾是「界」的化身,但在《無界的疆域》裡頭,在音樂與歌謠的宇宙裡,卻成為塗抹、模糊界線的依據。
《無界的疆域》以兩首卑南古調〈召喚善靈〉和〈崇高的創造者〉開場,這兩首曲目是整場音樂會裡頭編曲最為飽滿豐厚的曲目。鋼琴疊起磅礡和弦、壯闊的弦樂填滿血肉、低音鼓組震響如古神踩下的重重腳步,《無界的疆域》以堪稱典範的史詩音樂(epic music),鐫寫下神話的開篇。接著兩首卑南語教會歌曲〈聖聖聖〉和〈上主垂憐〉,略為減列伴奏的配重,但仍維持著一定的厚實感。
越過眾神的巍峨身影,《無界的疆域》在接下來的篇章大大刪節編曲的厚度,以較為簡約、分散的配器打造聲響的空靈感。觀眾得以更清楚地聽到桑布伊在不同音區共鳴位置的微妙差異,以及樂句漸弱處細膩而幽微地收束,重要的是,除去配器與和聲的華麗裝飾,更能感受《無界的疆域》意圖透過音樂傳達的訊息。
桑布伊在《無界的疆域》演奏了四把不同的鼻笛,一把來自北美洲、一把他自己手工鑿製的作品、一把史前博物館出借的收藏、和一把在淡水紀念品店買到的百元伴手禮。四把鼻笛彼此在時間、地域、製作技術等面向都有著極大的差異,卻在音色、律制上都出奇地相似。特別是收藏於史前博物館穿越百年歷史的古老鼻笛,不只在音準上毫不遜色,就連音色都比其他把更為集中圓潤了些。來自數世紀前的久遠聲音再次奏響,卻彷若與當下的時空毫無距離。
來自古今中外形制相仿的樂器成為鬆動「界」的突入口,而音樂源於人心感於物而動,《無界的疆域》要真正實踐「界」的跨越,仍得由「物」回溯於「心」。
《無界的疆域》最為獨特的一首曲目安排,是以閩南語演唱的滿州民謠〈狩牛調〉。歌詞敘述一位常在屏東與東部原住民交易的閩南人,意圖穿越中央山脈前往臺東發展事業,卻因旅途艱難、水土不服而無功而返。
〈狩牛調〉的背後是過去曾經曖昧的原漢關係。有很長一段時期,恆春和枋寮是平地人與山地原住民交易物資的集散地,包括居住於東部的原住民也常跋山涉水來到屏東,以部落的織品或獸皮向漢人交換礦石或金屬製品。
以〈狩牛調〉漢人主角的視角出發,臺東是滿山珍寶的富庶之地,這份想像讓他意圖穿越山脈縱錯的界。而回到〈狩牛調〉的歷史現場,山地原住民之所以不斷往返平地,也是為了那些無法以狩獵或栽植獲得的事物,投入交易的迴環。
中央山脈是臺灣最高聳的(實體的)界。〈狩牛調〉是旅人越界的行跡,踏著歷史而來,無論在歌曲之內或歌曲之外,都描繪了界的此端對彼端的嚮往。而這種壯遊的癡迷爛漫與其衍生的疲憊不堪,似乎又隱約呼應著人類社群不間斷地,向繁榮和富庶聚攏的進程。〈狩牛調〉講述的故事或許久遠,卻幽微回應人們為了生存而不斷移動越界的苦旅。
經歷信仰和神話的梳洗,歷史和族群的回望,《無界的疆域》最終返復歸藝術家自身的生命。在整場音樂會中,桑布伊不同時期的創作裡頭,每首歌曲各自有其凝望的對象,但大抵不脫他對自然及土地的觀照與鍾愛。卸下歷史與信仰的繁重思考,《無界的疆域》回到桑布伊從腳底至內心,生生不息的能量循環。在歌頌森林、風、及河谷之間,桑布伊始終在凝鍊之間帶著一種玩心,在馳騁山林的同時閃爍著自由的光彩,那是他與故鄉、親族、家園之間緊密不分的羈絆。純粹的情感自然地感染台上台下的眾人,毫不費力。
再次返觀《無界的疆域》的命題,或許桑布伊做的不是界的「消弭」,而是界的「擴張」。用一種毫無保留的擁抱,將所有可觀照的他者儘可能地吸納於自身。當界被拉伸、被延展至非我的邊際之外,便成就了「無界」。無界的疆域成了音樂與歌謠的遊戲場,圍繞著不熄的篝火。
《無界的疆域》
演出|桑布伊Sangpuy
時間|2025 10/18 19:30
地點|國家音樂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