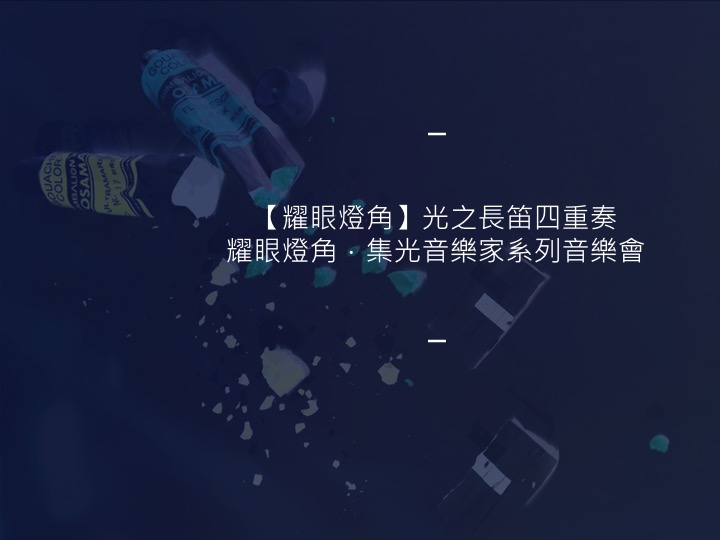
憶起大學時期,曾聽過一位教授講述他的「偏門哲學」,我至今印象深刻:在學術研究中,主流大宗的題目雖引人入勝,但前人成果豐碩,後輩畢竟難以超越;反之,最好投入那些尚在發展階段的冷門領域。於是,他留學柏林時研究中國笛子的聲學機制,冷門加冷門,果然迅速畢業,如今也做出一番成績。我認為這種「偏門哲學」對於所有領域都受用無窮,也特別適合用來談這一場特別的《光之長笛四重奏》音樂會。
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狹義的)長笛重奏並非主流室內樂編制,它在近一世紀才漸受寵愛,因此許多作品出自當代作曲家之筆,筆墨未乾且曲目文獻不算寬廣。而長笛重奏專場演出並不常見,專門的室內樂團隊則更是稀少。此外,同名的表演團隊「光之長笛四重奏」團員劉伊容、歐珈妏、鄭宇泰及張維紓全為青年音樂家,從他們的學習背景及生涯階段望去,也能理解他們為何投身探索這個新近且小眾的另類曲種。
長笛性能的思索與突破
在音樂會起初,就能聽到他們對於長笛性能的思索與突破。一開場,鄭宇泰兩首創作曲《擊敗節奏》、《上下顛倒》首先亮相。除了如其名所述,曲子穿插大量的複雜節奏之外,更值得注意的是曲子裡大量如呼嘯音(Jet Whistle)、打舌(slap)或Beatbox吹奏等特殊氣聲效果,【1】用來製造充滿動能的打擊節奏。這其實是要彌補長笛重奏本身的不足:長笛家族多為高音樂器,而中/低音長笛仍在不斷改良當中,因此低音缺乏可說是長笛重奏的一大硬傷。因此,使用氣聲技巧作為打擊樂器也等於彌補了這項缺陷。
除了長笛四重奏,他們也靈活地改變編制,演奏長笛三重奏、鋼琴與長笛四重奏等,以及不同長笛樂器家族的作品。當代作曲家貝夫汀克的《頻率—天際冥想》(H. Beeftink: Frequency)及麥卡爾《花之組曲》(C. McMichael: Floris)是兩個鮮明的例子:前者採用短笛、長笛與中音長笛,善用長笛泛音較少的特性,營造神秘如光的和聲色彩;後者則是當天創作手法最傳統的調性作品,旋律優美且平易近人,配上鋼琴家游適伃的合奏,四位長笛家都有各自的主奏秀段。
所有曲子裡,最早的作品則是十八—十九世紀作曲家庫勞(F. Kuhlau)的《g小調長笛三重奏》。這首樂曲有長笛名家工藤重典、Patrick Gallois及Philippe Pierlot的名演版本,是長笛重奏的名曲之一;此外,《小星星變奏曲》也是1991年眾多長笛大師改編演出的譜版,不難看見青年長笛家們與前輩對話、承接歷史的意圖。
演奏的巧與不巧
不過,即使有著精巧的曲目安排,演奏家本身的吹奏表現仍值得檢視。在整場音樂會中,穿插了唯一一首長笛獨奏曲:小倉大志的《星降之丘》,由近來活躍長笛界的歐珈妏擔綱獨奏。不論音色控制、上下跳音準確度及音樂性都十分成熟,在優雅法式風格中能兼顧表現力,是一位能夠好好期待未來發展的演奏家。相較之下其餘三人的演奏表現就不是那麼亮眼,例如鄭宇泰雖有傑出的長笛延伸技巧,但他吹奏庫勞《三重奏》第一樂章有時樂句零碎,音樂性平平;要論整體演奏表現,劉、張二人雖然穩定,但也非頂尖。
提到這些,其實我毫無不敬或詆毀之意,反而藉此面對了一項非常務實的問題:樂壇茫茫,和自己學經歷相仿的音樂人如此之多,我們該如何脫穎而出?如何找尋自身的藝術定位與獨特市場?回答這些問題,其實也就掌握了《光之長笛四重奏》的整個圖像。
打不過前輩,那就另闢蹊徑
我對長笛重奏的曲目文獻認識有限,不過單從選曲來看,可以發現多數曲目皆以通俗、流行為取向。打從一開始,他們就決定面向一般大眾,而非嚴肅的學術圈或演奏界;從當日的觀眾組成、以及他們歷來的活動性質而言,也確實如此。當今國內的嚴肅長笛音樂——包含經典曲目的詮釋及當代作曲發表——許多由音樂院系教授或中生代音樂家所執掌,青年音樂家其實並無太多發展空間;反過來說,流行與大眾化則是一直有待開發的當代音樂文化另一側面。
如此看來,光之長笛四重奏的音樂家們投入小眾曲種、面向通俗音樂、甚至投身樂曲創作並推廣當代演奏技巧,改善長笛重奏問題——打不過前輩,那就另闢蹊徑。他們並未也無意極端地走向如華珮或大衛蓋瑞(David Garett)那般的完全流行化,而是遊走於長笛領域與通俗流行之間,謀取其中的折衷路線,不離自身所長,也另尋處女地,是相當聰穎的選擇。
我不會說這是委曲求全或投機取巧的行徑;恰恰相反,不管是為自己爭取曝光機會,或是真正投入該曲種的探索,這都是拓寬現有長笛論述(discourse)、提升自身話語權的明智之舉。況且,也並非每個人都一定得當上獨奏家或長笛教授不可,關於音樂的職業與定位,人們不應如此自我侷限。
關於長笛重奏的前世今生,也許還有許多歷史瑰寶有待探索。如十九世紀名聞遐邇的杜普勒(Franz & Karl Doppler)二重奏,甚至更早的文藝復興合奏(Renaissance consort)也不無可能。不論如何,奠定現今樂壇生態的中、老生代正在凋零(例如,育才無數的英國長笛大師William Bennett不久前才與世長辭),未來的古典音樂將有何種樣貌,我們無從得知;今日的偏門,也許終將變成明日的顯學。
註釋:
- 此處僅憑音樂會當下的聆聽印象,其實無法確定他們採用何種技法。依歐珈妏的說法,他們主要採用Beatbox長笛技巧,然而應有其他技巧同時被採用。
《 【耀眼燈角】光之長笛四重奏》
演出|光之長笛四重奏
時間|2022/08/27 14:30
地點|國家兩廳院演奏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