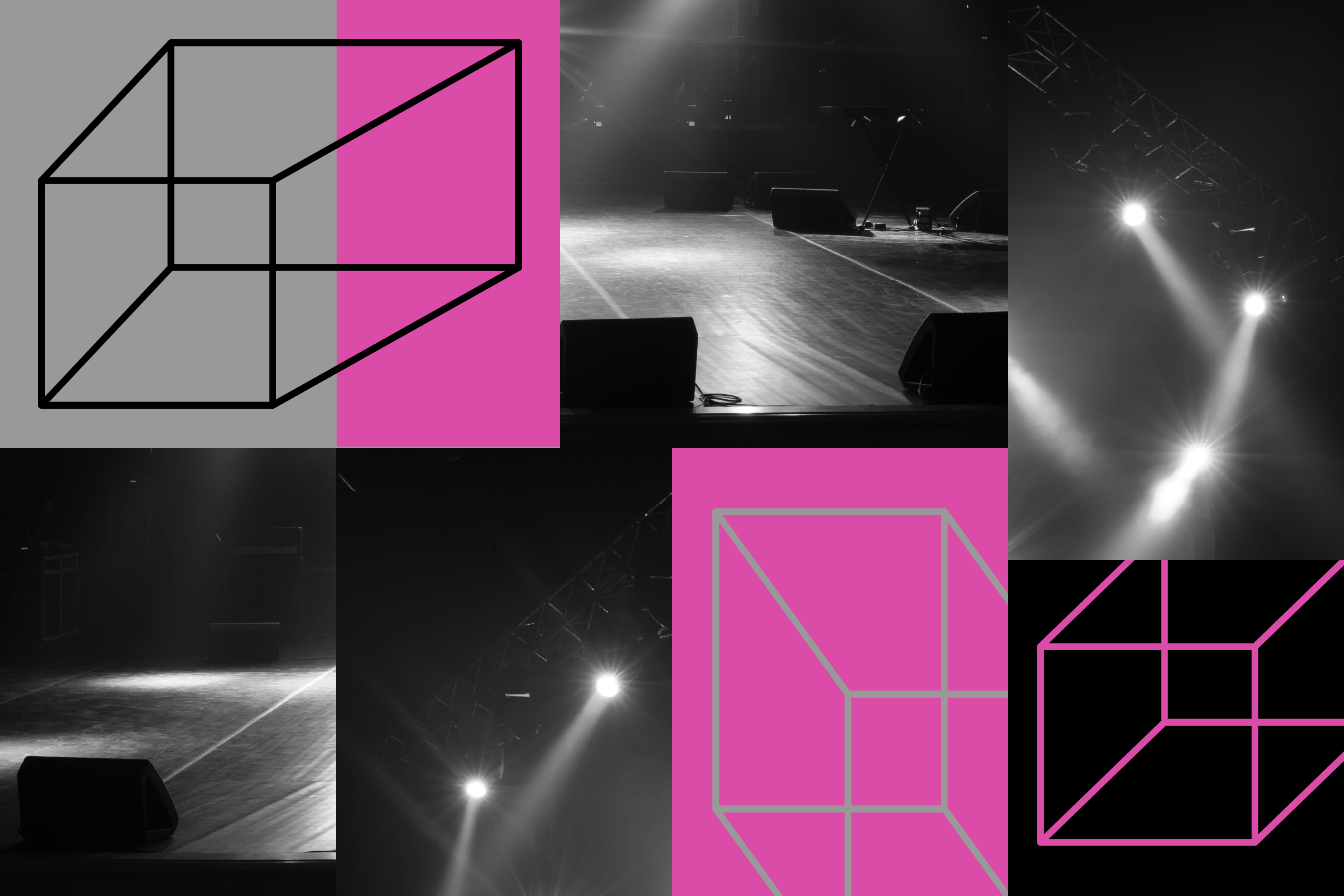
邁向第十五屆的臺北藝穗節首度轉由臺北表演藝術中心主辦,雖然在北藝中心自身營運體質尚未健全的情況下,2022臺北藝穗節今年的操作模式——不論是使用者體驗最前端的節目官網設計或是觀眾回饋平台的建置,都難以稱得上令人滿意,但總歸是悄悄地結束了。
為什麼要強調是「悄悄地」呢?因為在夏天疫情趨緩之際,前兩年因為疫情肆虐而沒得演出的眾多節目,一個個都像是抓到了救命索,摩肩接踵的複演場次把全島北中南的場地都塞得滿滿的。再加上國表藝系統主辦節目和北藝中心自已的開幕季和雙藝術節(臺北藝術節和臺北兒童藝術節),國內劇場消費者的娛樂成本——不論是荷包或是時間都吃不下這麼多節目。在客觀環境已如此不佳,行銷能量又未能順利傳播給觀眾的情況下,2022臺北藝穗節很自然地被邊緣化了。
臺北藝穗節隨著夏天默默落幕,但與此同時,其他縣市的藝穗節正熱鬧著。苗栗店仔藝穗節今年邁入第二屆,三個周末、六組節目在健身房、咖啡廳、餐酒館等苗栗市的生活空間輪番上演。臺東藝穗節則觸角遍及全縣,以「市區」、「山線」、「海線」、「南迴」等地理概念劃分,演出歷時整整兩個月。
至此,藝穗節已不是臺北人的專屬品牌,可以想像這或許會發展成一個綿長的趨勢,每一個都市、鄉鎮都可能加入藝穗節的隊伍,挑戰城市容納藝術的潛力與極限。但與此同時,一個問題意識在我腦中萌芽——它們真的都算是「藝穗節(fringe)」嗎?
「不審查」才是藝穗節的核心精神
長久以來,國內對於「藝穗節」這樣的活動,觀演雙方十分有默契地把關照的重點放在「非典型表演場域」這個呈現形式。然而只要對藝穗節發源地——愛丁堡藝穗節有一些粗淺的認識,會知道其實愛丁堡藝穗節裡其實多的是在正規劇場演出的節目1。
「fringe」一詞原意為「邊緣」,源起於1947年有8個劇團未能通過愛丁堡藝術節的審查,他們自立自強在藝術節外圍尋找合作場地、聯合演出,促成第一屆藝穗節的誕生。自此之後的愛丁堡藝穗節,只要能自己找到演出場地,任何團隊、單位都可以成為藝穗節的一份子,獲得一個作品露出的平台,其他包括製作、售票,一概自行負責。換言之,「不審查」才是藝穗節的核心定義。而那些新奇、獨特的展演空間和觀演形式,至多只能說是前者衍生的副產物。或許造就了藝穗節接起「劇場」與「日常」兩端的獨特魅力,但終究不是藝穗節最基礎的精神。
臺北藝穗節姑且還算復刻了這種不審查的策展形式2,但是諸如苗栗店仔藝穗節、臺東藝穗節都還是請了「專業委員」對徵件而來的節目做了評選,把「演出主題構想與藝術性」、「演出場次規劃及內容可行性」等項目作為審查的標準3。除此之外,更進一步對演出的場地做了限制4。這與崇尚自由發揮、不設限制的「fringe精神」,無疑相去甚遠。
而從這些藝穗節的節目組成、演出形式、宣傳著力點來看,他們大多是把重點放在「非典型場域」和「新興創作者」5這兩個面向。前者應是從臺北藝穗節借鑒而來,後者則多半是從「藝穗」兩字的字面意義出發,有扶植新秀之意。甚至於,後者可能才是這些地方單位之所以籌辦藝穗節的起心動念,而「藝穗節(fringe)」這個詞語不過是(對主辦單位和民眾來說)最現成、也最容易操作的概念6。一言蔽之,我們可以大膽而粗略的畫出這樣的先後邏輯:臺北先仿效歐陸城市舉辦藝穗節,國內的地方政府又意圖複製臺北的經驗而打造自身的版本。
從英文到中文、從歐陸原生到臺灣仿效,「藝穗」一詞的質變所反映出的,其實是這些在國外由民間自發的藝術節慶,在國內被官方「收服」之後,公部門主事者是如何從中「擷取」自身最想要、最需要的那一部份,最終留下了外殼的形式與名稱,內裡還是回到策畫端與表演端之間,無盡搏弈的茶壺風暴。
不是藝穗又怎樣?誰確定哪個月亮比較圓
當然,沒有人不樂見更多的藝穗節、藝術節在更多不同的地方發生,我們永遠都需要不同的平台讓每個創作者都有機會被觀眾看見,我們大可以把前述fringe不fringe的種種都視為一個美麗的錯誤。但同時不能忽視的,是倘若官方最終只以自身的政治目的為導向去操作這些藝術節慶,有朝一日難免不會弄巧成拙。
今年度的「白晝之夜」無疑是個血淋淋的例子,這個源自於歐陸、最初也是由民間藝術策展人發起的活動,原本欲求在夜晚百業歇息的時候,把原先承受諸多規範限制的城市景觀「打開」,在毫無規則的一夜狂歡之中「把城市還給民眾」,藉由藝術把所有對城市的想像還諸城市。
而自2016年舉辦至今,臺北版白晝之夜雖然少不了為公部門喉舌作態的批判,卻也逐漸建立出自身的品牌。但今年的白晝之夜卻限縮至北藝中心周邊的士林區塊,其策畫概念幾乎可說是完全導向於觀光需求。試問,遠近馳名的士林夜市有哪一日不是時近午夜仍亮如白晝呢?這樣空有其名的白晝之夜,被批評失去白晝精神、淪為士林觀光嘉年華,也不是什麼多令人意外的事。7
回到藝穗節,這篇文章讀來似乎充滿了批判,但我仍然要強調,我永遠樂見於更多的藝術活動在國內發生,特別是藝穗節這般為年輕藝術家設身著想,並且把他們的作品帶到與觀眾最接近的日常場域。這些遍地開花的藝穗節即便在徵件標準或平台媒合等操作模式上與真正的fringe festival大相逕庭,卻仍不啻為「新鮮創作者嶄露頭角的最佳解8」。
只是說到底,為什麼一定要冠上「藝穗節」這個名稱呢?就沒有別的概念可以乘載主事者扶持新秀藝術家,同時以藝術改造城市景觀的這份美意嗎?倘若身為藝術節核心的主事者與藝術家,有足夠的經驗和能力把作品裡的精神和故事傳遞給觀眾,進而把這些能量還之於城市自身,那麼我們又何必一定得緊抓著「藝穗節」這個舶來品?
最後請容我任性的許願:臺灣自身閩客文化生長而出的民俗節慶,也有其不可忽視的藝術能量,卻始終與所謂的「當代藝術創作」彷彿身在兩個不同的次元。基隆中元祭、嘉義北港藝閣、苗栗爖,這些族繁不及備載的節令活動長久以來也乘載著賽陣頭、瘋藝閣等民間自主「同台競藝」的藝文匯演。如果我們仍然期待當代藝術有一日可以在大眾的生命中扎根,這些與社會已有歷史連結的節令活動有沒有可能成為另一個可以施力的平台?
或許我們可以轉換一下視角,從「外國的月亮比較圓」試著慢慢調整成「月是故鄉圓」,在仿效歐美經驗的同時,重新思索藝文活動於社會中的意義與鏈結,進而找到當代藝術在其中可以安放自身的位置。屆時,或許「打造專屬臺灣的藝文節慶」也能成為一個不那麼遙遠的可能。
註解:
1、即便是如今年的臺北藝穗節,也有如萬座曉劇場、政大傳播學院劇場這樣的正規場地。
2、臺北藝穗節對節目形式唯一的限制,是「本活動以鼓勵藝術創作為主,社區活動或才藝發表會,請勿報名。」,見2022臺北藝穗節中文簡章第壹拾條第一項。
3、見2022苗栗店仔藝穗節複合式展演計畫,演出計畫徵選簡章第陸條第二項;及2021臺東藝穗節演出計畫及駐村藝術家甄選簡章第十一條。
4、苗栗店仔藝穗節的模式是先徵集演出場地,場地定案後,再告訴甄選團隊可以選哪些場地。而臺東藝穗節則是甄選團隊可以自由選擇任何一個縣內場所,但是又明文規定演出場地「不得為本縣既有之劇場空間」。
5、事實上,臺東藝穗節每年都有部分節目為舊作重製,這些作品在參與此藝穗節之前,大多已經累積了一定演出的經驗和迴響,只是在臺東的非劇場空間做了一些限地概念的修整與再創作,與所謂的新興「藝穗」團隊稍微有些不同。可以說,臺東藝穗節的策展理念仍是以「非典型場域」作為最核心的訴求,透過徵件而來的作品為對臺東獨具特色的地形地貌重新詮釋,進而獲得自身的獨特性。
6、有一個十分有趣的例外是宜蘭的羅東藝穗節,這個舉辦亦超過10年的活動,前面幾年的英文譯名使用的是「carnival」這個詞,近幾年才改成「fringe」。而這個節慶的主要內容是各個社區、學校的才藝聯歡會和踩街遊行,就我看來「carnival」這個詞還比較符合它的內涵。
7、事實上,還有很多案例可以用這樣的生產脈絡去理解。譬如近年各地風靡的地景藝術節(諸如桃園地景藝術節、宜蘭壯圍沙丘地景藝術節、苗南海地景藝術節、東海岸大地藝術節等等,族繁不及備載),恐怕多半也是地方政府讓自身變得更「好打卡(instagramable)」的振興政策。
8、語出張輯米〈給未來的藝術節——談臺北藝穗節〉,但張籍米也提及這仍是建立在「不審核」的前提上,讓創作者「不需要很會寫企劃案,不需要學院科班畢業,不需要認識名人,不需要家裡有錢,就能參加以及被許多人看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