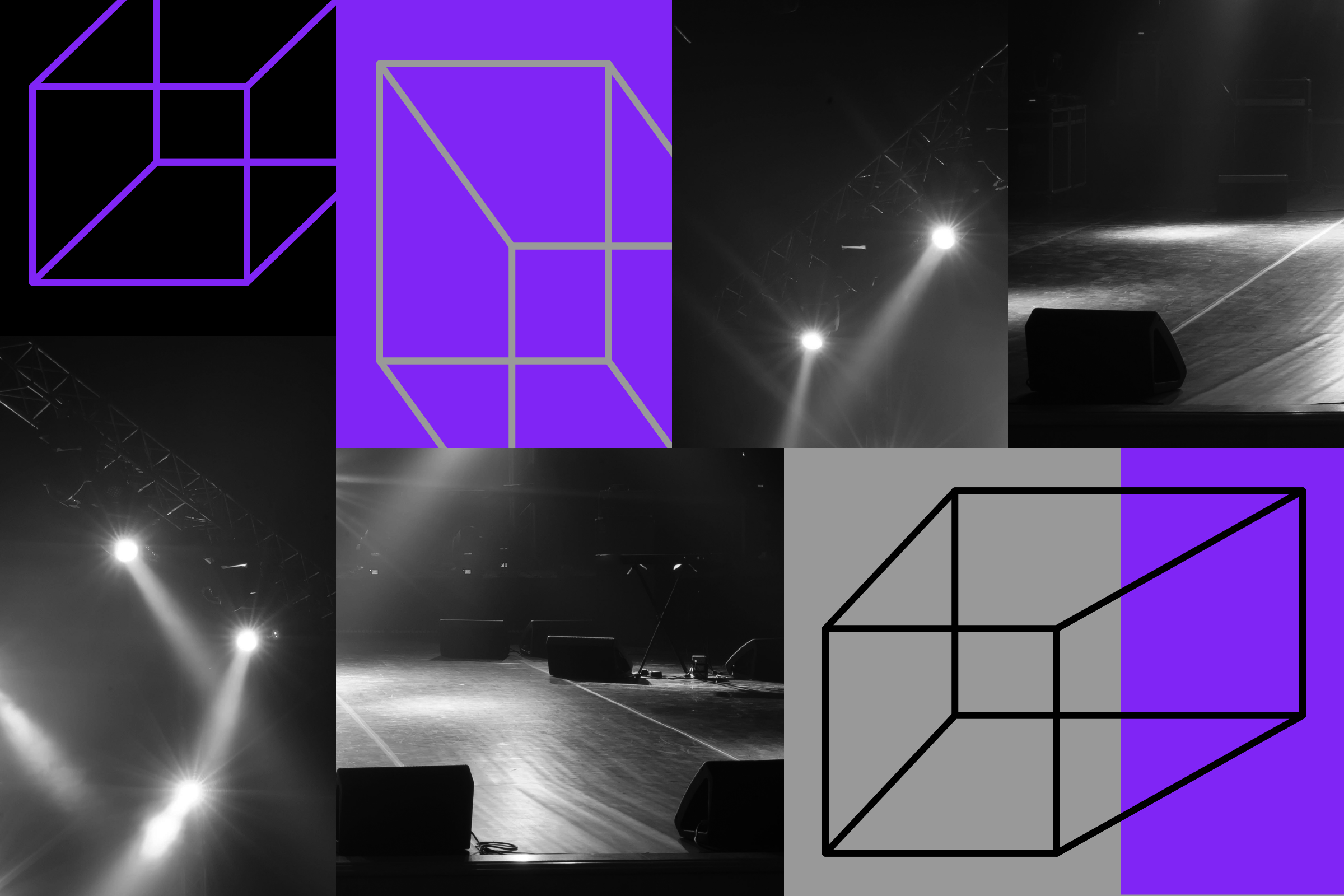
文 陳佳伶 (專案評論人)
當舞者的身體縱身一躍跳下舞台、遁入尋常風景,我們會期待看到的是有別於台上的身體形象,或猶仍是空間異地轉換後的舞蹈顯影?「舞蹈風景」平台在台灣、新加坡與香港三地,分別由四個場館所委託,創作屬性多樣的影像,引領觀眾思索日常之於舞蹈、身體之於影像的特立與相容。
《我在,不在?》為新加坡濱海藝術中心所製作作品,正片開演印入眼簾,宛如家庭劇情片現場,不落俗套的是無論敘事發生,與情節推演都是以肢體動作,及舞蹈身體作為表達,絲毫未有通俗劇的叨絮台詞或雜沓旁白,能觸及生活煩擾的唯有那躁動的身軀,首幕即見大腹便便又大汗淋漓的一景,手足無措的分娩場面襲來,幽暗迫近的鏡頭無法安放片刻的從容,慌亂中不知從腹腩抑或兩胯間,升起一顆紅氣球,自從50年代的法國導演—艾爾伯特.拉摩里斯(Albert Lamorisse)拍出了經典短片《紅氣球》(Le Ballon rouge)之後,這顆氣球不時流轉在各式影像中,象徵著童年的產出與再現,在電影語彙裡,易於讓人聯想起孩童時光的純真與苦澀,物件運用無疑是為觀眾點出,作品源於一則童年的回憶,不避俚俗地從平凡的家庭場景起始,反轉引入記憶的雋永。
家屋空間的人物關係主要座落在母與女,另有父親獨立的身形,母女的身分由舞者一人分飾兩角,並運用了同樣屬於影像語言的身替(Body Double)手法,在兩者必須同時出現於鏡頭前時,迎向視角的女孩由舞者本人擔任,背向觀者的母親由他人成為替身,藉由狀似肖像的特寫鏡頭,特徵化舞者獨有的臉上印記,讓我們肯認扮演她們的實為同一人,如此形塑出重複疊加的身影,透過鏡頭的協助演示出唯獨個人的群舞,這款子從母出的生命延續與關係緊密,採取影像媒介的直接調度,其千絲萬縷的縝密強度,全然不減損於在織物拉扯牽動中的表現。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所出品的《沖流》則使用另一種身體換位的方式,來展現人我關係,由一衍生而出的化身,白衣過隙忽而引來闇影如梭,各自在兩位舞者身上竄動,又在鏡像萬花筒中交織、映照彼此的身體維度,當個體隨著潮汐細數時光推移,回到獨自一人時,發現已非原我的自己了。

沖流(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提供)
這種身形拓印叢生的視覺印象,從《我在,不在?》作品中也顯現端倪,相應於母與女將對方的身體凹摺縫合,三人一組的黑衣女子以相似的翩然外型,哀戚面具般的同一表情降臨母親的房間,三者的身體編排,與影像中的走位,讓她們吻合像是死神又是哀悼者的形象,迎面而來這個家庭的噩運,加乘以三的形體,無論她們垂手反掌或是步履輕移,都以量體般的形式瀰漫與充盈家屋空間,揮之不去的聚散離合自此駐足其中, 時鐘滴答隨行 ,鬱滯濃重的氣息終於突圍出密室空間的牆籬,尾隨鏡頭推移我們終於瞥見家庭居所的外部,卻也見證了又是三個南亞面孔的建築工人,與視線錯身,入境登陸這個隱蔽的居所,除了側寫新加坡的人種共處現況,也將家從棲身之處變成現代化工地,家的記憶顯然將不復存,家還能是家嗎?當家屋的樣貌跟著影像所見之處,愈益完整之時,竟也預視了它未來的頹圮與衰落。
父親的角色在這部作品中舉重若輕,多數在屬於他的父系空間佇立著,穿脫他的工作服,掌控著一家生息,若是生計擁有餘裕,時間就會順時滴漏,反是生活坎坷難過,一刻鐘猶如走了一世人,時間充數在父的房間中,當然也浸沁在他的身體內裡,創作者在人父身上演繹著一段「定靜而後能動」的過程,在同一鏡頭下由日常行為逐漸過渡到表演身體,我們能明白他的啟動存在有相應的契機,他將肢體放大到符合角色的情緒,或說是總體影像的需求後,就讓身體收斂恢復到日常的疲軟,相較於表演性總是在高張狀態,這種身體的形象是相對如實與恆常的;而他的身體又是展演式(performativity)的,影像調度下的空間與物件,都已為角色配置完成時,人物的身體幾乎就是行動本身,不必編造父親之舞,即可用身體宣稱他在這個家的位置,父親的羈絆不是在與對象綿密的關係上,而是他必須為家人分配家內的時空,並操勞自己的體魄。 無論作品的風格是著重敘事,或是特寫關係,身體都將以順應或抵抗的姿態安放自身於影像序列中。
舞蹈風景委創計畫中的另外兩部作品,《我・我們》以充滿視覺與聽覺衝擊的表現力,含納整體影像;《當下》運用不同的舞蹈類型與場館空間產生共鳴,共同擘劃出舞蹈影像的異質光譜,開創言語之外的身體敘事,舞蹈透過影像的折射,既可返景深入舞台的表演性,亦可復照於日常的身體感知,期許觀眾如我在屏幕間覺察自我的容身之所。 
我,我們(布拉瑞揚舞團提供/攝影唐健哲)
當下(臺中國家歌劇院提供)
《我在,不在?》
演出|舞蹈風景計畫
時間|2023/03/04 12:00
地點|臺中國家歌劇院角落沙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