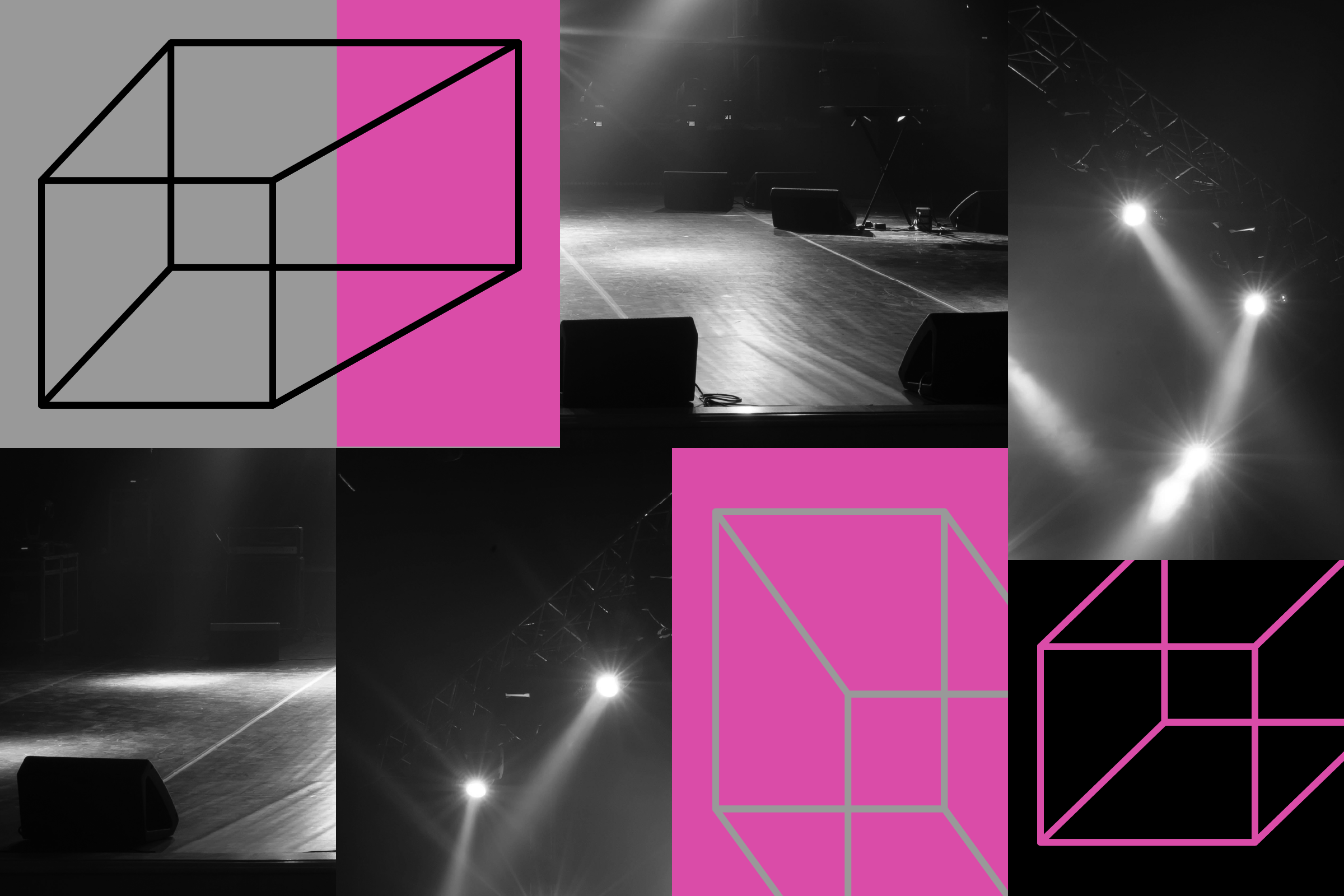
年度魔王交棒
合契於劇名,恰當應用光影偶戲的說故事開場,敘說魔王鎮匯集著各式各樣故事中常見的魔王,年度魔王代表又是大野狼被選上,可是大野狼卻想退休交棒了。此時自以為天不怕地不怕的小魔出現,誇下海口要成為取代大野狼的大魔王。
至於如何成為大魔王,以開場的歌曲〈歷史上的大魔王〉來思考,歌詞中提到要「懂得製造驚嚇,除此之外,還要懂計畫!⋯⋯懂得破壞驚喜,除此之外,還要懂人心!⋯⋯懂得創造黑暗,除此之外,還要承重擔!⋯⋯懂得操控影子,除此之外,還不能偽裝!」這彷彿是當一個大魔王的武功秘笈,但每一條守則的曉諭,卻未完全在接下來的劇情中發揮,反而聚焦到「要擁有自己專屬的影子」這件略顯抽象的事情上。
什麼是「要擁有自己專屬的影子」?大野狼舉自己的經驗,敘說有一次差點溺水,之後自行掙脫絆住腳的水草上岸,因此他的專屬影子牌上就有了水草的圖案。其他角色也各自表述凸顯出自己如何以勇氣得到專屬影子後,這齣戲最大的問題卻也由此而生。
大魔王為何為惡
一個人會作惡多端成魔,姑且不論是否服膺荀子「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的性惡論,但依我過去在少年觀護所擔任過榮譽教誨師教學的經驗觀察,大部分為惡者入獄者還常見一時情緒管理失控,或欠缺道德自律,甚至只是刻意想被關注,選擇了惡這一端的行為表現。
但這齣戲的故事將勇氣與擁有自己專屬影子的設定連結,以此勇氣作為成魔的起點,不僅把勇氣的正向意義扭曲,無形中還把人一生中面臨的其他危險困難和失敗都排除,因為已經有專屬影子有了勇氣似乎一切都可操控,難不成這是一個免死金牌打造了人金剛不壞之身?
尤其接下來又透過長老一角正經提出「情緒陰影」來解釋小魔無法擁有自己專屬的影子,就是內心的恐懼造成。這樣的情節導向偏離更遠更突兀,實在很難完全說服人。
除了恐懼,尚有其他「陰影」
心理學家榮格原型理論核心的「陰影」(Shadow)觀念,指出陰影是人無意識包容的一切,可能被自我排斥和否認。這齣戲的處理手法,是將小魔的陰影投射成Shadow熊――外表看來既不威猛可怕,內心卻又孤單想要有伴想被擁抱。
當我們看到小魔和Shadow熊這兩個偶各自被具體化作偶來操演時,不禁想先問為何用熊代替刺蝟、蛇、獅子、老虎⋯⋯其他外表也是威猛可怕的動物?當熊在1903年被物質化成泰迪熊玩偶形象時,熊的溫暖可愛形象深植人心,撫慰陪伴無數孩子成長,以熊作為小魔內在的陰影形象,以及小魔自身為何如同Shadow熊也是孤單想要有伴,在戲裡都欠缺明確的理由交代。
其次,這齣戲關於情緒陰影的概念,直接簡化同於恐懼,思維論述也顯得不夠縝密。心理學界常將人的基本情緒分為:恐懼、生氣、快樂、悲傷、感謝、厭惡、期待與驚訝這八種,同時具有正向與負面的感受。假設一個孩子期待愛而落空,依附的失落與創傷,情緒陰影的產生,硬說是恐懼恐怕無法全然掌握內在狀態。
若我們再回到榮格的源頭觀念,按羅伯特.強森(Robert A. Johnson)《擁抱陰影:從榮格觀點探索心靈的黑暗面》指出的「榮格最偉大的洞見之一:自我與陰影來自同一個本源,準確地相互平衡。創造出光就會創造出陰影,兩者相依共存。」1覺察、接納陰影,讓其平衡成自我的另一端,不必然就是要去克服消滅陰影,就某些層面來看,還具有創造性的行為與文化意義。例如一個坦然接受自己厭惡人際互動的自閉症者,讓自己安於靜默孤獨,也許可以將陰影投射到各種創作上去成就自己;這個自我整合的過程,就未必攸關於勇氣。
除了勇氣,兒童還需要什麼?
這齣戲最後讓小魔從討厭到接受Shadow熊就是自己的鏡像的轉化,歸因於得到勇氣,所以戰勝恐懼,然後放棄想成為大魔王,可以開心擁抱Shadow熊。只是這樣的套路,Be劇團過往的《膽小獅王特魯魯》、《達斯克部落――快樂鼠王國》等作品皆可見主角學習勇敢,面對困難這些雷同的題旨,一再重複出現時,創作者勢必要再慎重思考題材深度與廣度的開鑿了。
不過有些弔詭的是,看《小魔王與Shadow熊》刻意引用心理學概念,更直接將情緒陰影安進台詞裡,不難揣測編劇還是有意識想要讓兒童劇不只是稚氣可愛模樣的企圖心,可惜失手在失去「自然」的成人化,前述諸多邏輯概念與情節一廂情願設定,一切反而彆扭不自然了。
最後,戲中的編舞動作偏向當今流行舞,許多過於妖嬈扭動的肢體太成人化,並不適合在兒童劇中表演呈現。雖嘗試解放兒童劇長久以來被桎梏的稚氣可愛模樣,但我們要如何不矯柔造作的解放這個被成人僵固想像已久的模樣,純任天真自然去和兒童的想像接應,這是兒童劇創作者永遠要先面對審視的本質問題。
註解:
1、羅伯特.強森著,徐曉珮譯《擁抱陰影:從榮格觀點探索心靈的黑暗面》,台北:心靈工坊,2021,頁68。
《小魔王與Shadow熊》
演出|Be劇團
時間|2022/11/06 14:30
地點|文山劇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