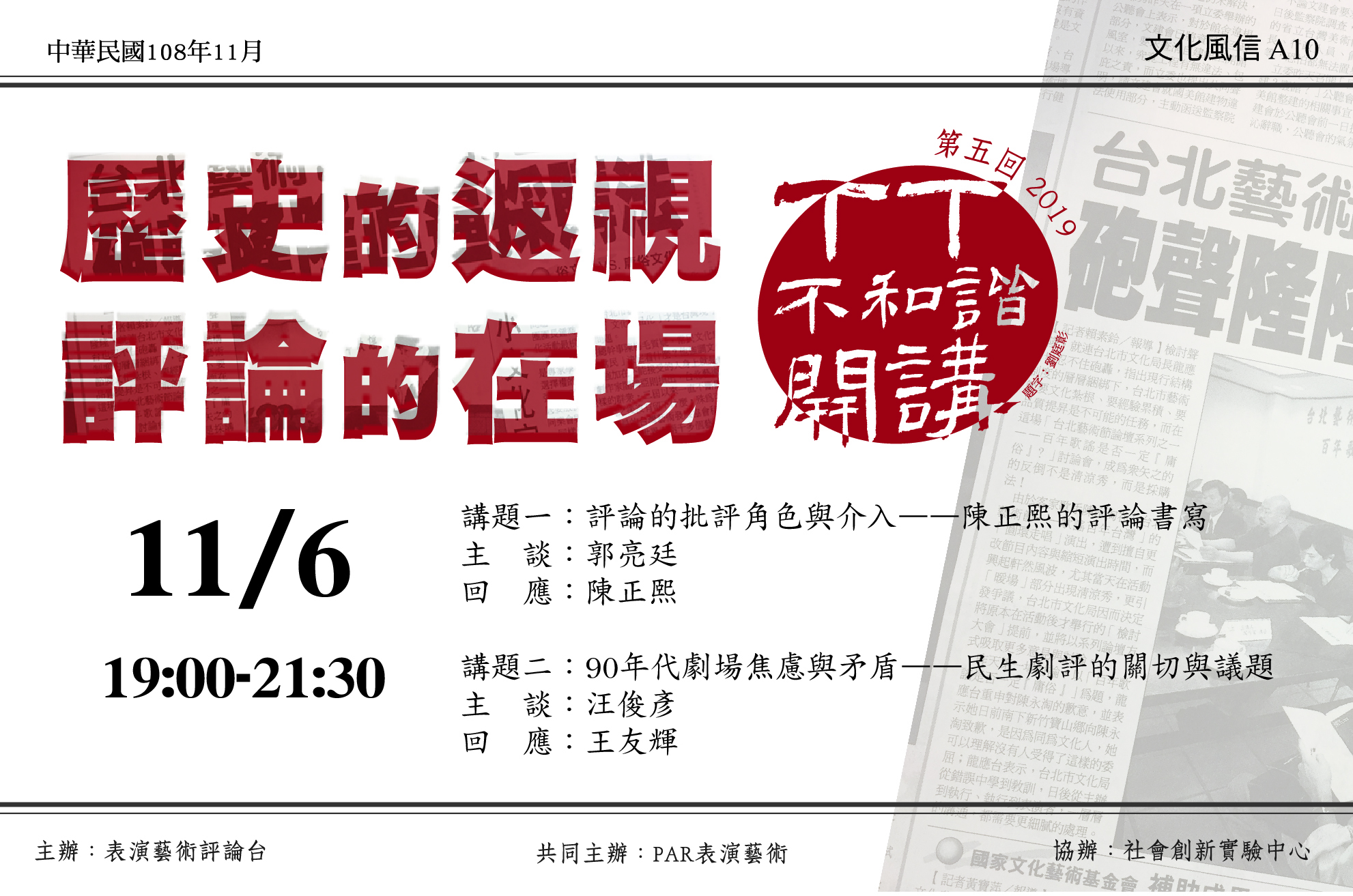
1996年末,田啟元剛剛離世,牯嶺街小劇場還要六年後才會啟用,而信義計畫區的新舞台幾個月後開幕。今日的華山文創園區當時還是城市中心的廢酒場模樣,南海學園的藝教館仍是表坊最常使用的演出空間之一,演出排練場也還作為許多小劇團的表演場地:民樂街的臨界點劇象錄、敦化南路巷內地下室的皇冠小劇場、屏風演劇場⋯⋯。約莫同時,民生劇評誕生,陳正熙、王墨林、周慧玲、李立亨、紀蔚然、蔡依雲、傅佳霖、王友輝等是最早的一批寫作班底,幾乎輪流定期每週刊登。1997至1999年間是民生評論第一個高峰時期,內容主要以國內製作為主,不僅僅觸及專業編、導、演、空間與設計評論、擴及美學、歷史、當代與在地意識的討論與小劇場的定位與續命,再到藝文政策與社區劇場發展種種。之後民生劇評加入更多舞蹈與音樂的書寫,然後戲曲也進入評論的場域。
第一批的評論者在開始進入民生劇評之前,幾乎全都具備戲劇、劇場或學術或實務的長期功底與參與。在其評論的關注取向,充分顯示出對於演出作品完整程度的高度要求,從製作的細節、劇本的對白語言、合理性與議題的處理、導演的手法、技巧、節奏與調度能力、演員的姿態、口條、成熟度與演技,再到演出空間、舞台布置種種劇場元素,成為這時期劇評的重要特色。也可能因為如此,表演工作坊、屏風表演班、綠光劇團、果陀劇團、台北故事劇場或優人神鼓等逐漸形成九〇年代末台灣的中產(?)、商業(?)、主流(?)演出,大多也是這時期劇評的關注焦點。當然對於八〇年代一路延續的小劇場創作,河左岸、臨界點劇象錄、差事劇團與金枝演社再到莎士比亞的妹妹們,或是台南的魅登峰劇團、華燈劇團、那個劇團,高雄的南風劇團、屏東黑珍珠劇團、台東的台東劇團,也受到劇評的關注。粗略地說,我們看到劇評一方面關注劇場的建制化,開始對於演出提出專業的劇場期待,從編、導、演的品質,敘事、行動、人物與形式的辯論,與如何掌握觀眾與演出效果等;另一方面,對風格迥異於標準或風潮演出的小劇場,其抵抗、美學、位置、延續或再生種種問題,亦是這時期劇評的核心觀照。前者面對的觀眾是一批越來越清晰的大眾或消費者,而後者則是極力想要繼續延續或維持一批越來越模糊的前衛劇場群體。
想要全面處理民生劇評仍需要投入更多的研究,現階段只能簡略地提出幾點觀察或思考的輪廓。首先,這時期劇評鎖定的書寫與閱讀對象都非常的精準。他們不只是觀戲的筆記,也不是喃喃自語的感想或是心情抒發;多所見到毫不保留地直指製作瑕疵與演出問題,評論對於表演已不是「很好、好、不錯、還可以、很差」等尚未標準界定的感受性分級,甚至不只是分析劇本與表演,而是豪邁地辨識與詮釋編導的意圖、語言與符號的意旨與創作的用意。或換句話說,人物角色具不具體、劇情合不合理、應該如何演、可以怎樣導得更好,這時的民生劇評提出了種種專業的閱讀;就觀察劇評與創作的關係而言,這評論要求,其實某種程度直接推動了台灣今日主流劇場的何謂專業演出的形構與認識。
其次,我也發現所謂「中心vs.邊緣」、「主流vs.另類」、「創新vs.老套」、「市場vs.抵抗」,甚至是「大中國(華)vs台灣」種種近似對立性區別的出現或鞏固。一方面,我們可以理解成台灣戲劇場域的愈臻龐大,台北作為都會人口最集中處與城市發展最迅速之所在,在劇場界「中心」的架勢亦趨鮮明,同時表演的美學、風格與立場等也分化出來。但或許也可以重新提問,這種類對立性的認識,無論是美學的,立場與位置的,地理的或資源的,通常作為有效而迅速的辨識身份認同的方法,但是不是同時也持續生產而再次有效地歸類了歷史種種尚不可分類、或不能分類的劇場創作與發聲位置。舉例來說,九〇年代的小劇場最常被提及某種對立式的抵抗與收編論,有沒有可能有種認識可以是:標記一個抵抗的小劇場正好是收編所需要的;或許再以一個自我提問作為這篇前導文章,晚些時候民生劇評中以同樣專業面貌現身的戲曲評論,是如何從八〇年代使用、操演傳統,開始進入辨識傳統與指認的專業劇評,這種指認的學術性如何再進一步成為生產創作的一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