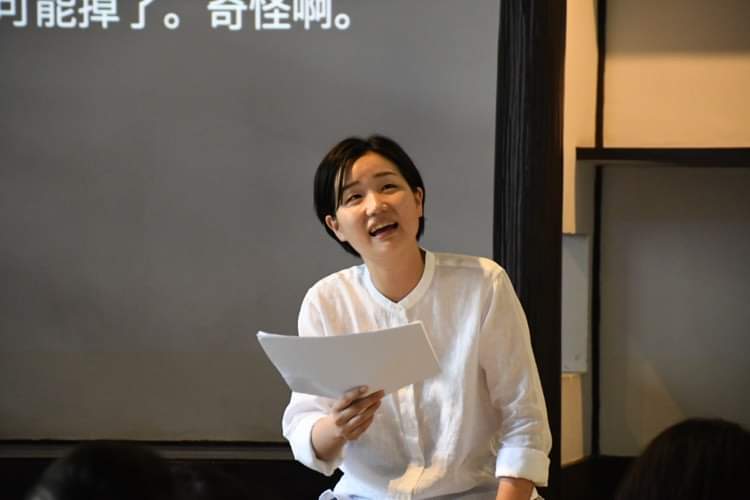
許仁豪(駐站評論人)
這是編劇濱邊風的單人讀劇表演,場地在剛變身為台灣文學基地的前齊東詩社,內容關於二戰前後流離於中國、日本與台灣的幾位老奶奶認同故事。
悶熱的台北盆地假日午後,我與友人信步到這個剛整建好的日式宿舍群,新穎乾淨的古蹟重建,新漆的味道未落,大大旗幟上寫著「不願被消失」,口號宣告著建築的重整與歷史記憶保存的重要關係,而記憶的復刻就在這個物理空間再造之中,既新且舊,是建構還是重現?是新創還是複寫?歷史現身之際,哪些被突顯又有哪些被遮蔽?
台灣本土化浪潮之後,「日據」變成了「日治」,過去被抹黑、妖魔化的歷史記憶,驗明正身,變成現代化起點,播種啟蒙的時刻。各種日本時代留下的建築物開始被搶救,整建整容,華麗轉身,變成了比日本更日本的文化消費場所,身體只要進入這些空間,一種觀光旅遊的興奮泉湧而上,掀開印有兔子或海浪紋的布藝窗簾,買一個宇治金時抹茶冰淇淋,不用去京都也到了京都。但在這種訴諸官能愉悅的消費化日本符號下,是否又遮蔽了哪些不堪的歷史與幽暗的過去?
濱邊風的發展中劇本《上游》選在這樣一個場域演出,固然借用場地的日本風情,但其內容誠懇面對政治暴力下庶民認同掙扎的議題,不啻直擊上述關於歷史記憶與再現政治的種種問題。

上游(九條劇濱邊風提供)
劇本呈現國族/身分認同議題
在京都九条地區長大的濱邊風從小與在日韓國人混居長大,她曾經一度以為自己就是韓國人,直到上學時刻到了,她才赫然發現自己是不折不扣的日本人,而自小一起長大的玩伴竟然無法與自己一同上日本人學校。在這個自我認同的轉折點上,她同時發現大人們對韓國人有著根深蒂固的歧視,她曾經試圖說服爺爺,卻發現無可改變,這深層歧視背後有著歷史結構問題,於是她把這段經歷寫成了劇本《我的毆吉醬》。
延續《我的毆吉醬》的身分認同議題,《上游》起源於濱邊風來到台灣學習中文,在過程中遇見不少活過日本時代前後的長輩,其中一大部分來自於她教授日文的廈門教會,在與多位長者近身訪談後,在這些現實故事的基礎上,《上游》以虛構的人事物和優美工整的文學手法串接而成。
劇本以第一人稱開始,千鶴小姐來到台灣學習中文,在一個悶熱的台北午後,突然的雷陣雨,她來到一座公園樹下躲雨,因此邂逅了高齡95歲的李雪音奶奶。千鶴以剛習得的中文隻字片語嘗試溝通,沒想到老奶奶說著流利卻口音古樸的日語,一場穿越時空的跨文化相遇因此展開,波瀾壯闊的歷史浪潮下,幾個老奶奶的私人記憶糾纏著時代殘酷的鐵輪之律。
雪音的家庭原來在戰前從中國搬至日本謀生,她於昭和二年出生於日本,並在日本長大,說得一口流利的日語,從小便覺得自己與日本人無異,直到中日戰爭爆發,在日華人處境日益艱難。有一次父親因為工作問題,被迫做出選擇,要不改日本姓名從此成為日本人,要不就返回中國,父母決定帶著小孩回返中國,但雪音的哥哥卻不願返回中國,於是改日本姓名獨自留了下來,雪音一家從此與哥哥天涯兩隔,不再相見。
返回中國後,雪音濃濃日本口音的中文讓大家認為她就是日本人,戰後的中國只要帶點日本色彩的一切都足以成為壓迫的緣由,雪音一家因此又萌生移民念頭,在親戚介紹下來到了台灣重新落地生根。
戰後的台灣,日本人走了,但很多人卻都還懷念著日本,甚至抗拒「再中國化」的新政策。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下,雪音認識了新的台灣朋友櫻花,一個活過日本時代,只到過日本旅遊一次,但即使光復之後,依舊深信自己是日本人,嚮往日本的台灣女子。櫻花在雪音身上投射了關於日本的一切,忽視了雪音其實是移民日本的中國人的事實,甚至介紹了滯留台灣,不願返日的日本老師給雪音認識。
原來這位日本老師在戰前與台灣男友相戀,卻不被眾人看好,原本約定私奔,但是日本戰敗後,男友沒有赴約,日本女老師留了下來,在等待之中生下了女兒千夜。千夜自小在台灣長大,說著流利的閩南語與日語,她是一個從沒去過日本的日本人,在台灣長大,卻從沒見過台灣父親的時代孤兒。

上游(九條劇濱邊風提供)
桃太郎被老奶奶撿到之前,是哪國人?
故事交織在雪音、櫻花、日本老師與千夜四個人物之間。人物設計的詩意象徵功能,大過寫實細節的鋪墊,不消說,雪、櫻、夜與鶴,這些名字背後的意象鮮明,一方面乘載濃濃的日本風情,一方面又透過意象勾連人物認同掙扎下的視覺化情感。
濱邊風擅長運用歌謠與傳說的詩化意象來說故事,串聯整個故事的核心意象便是日本的《桃太郎》傳說,那顆飄在河面上孕育著桃太郎的桃子。
故事一開始當千鶴與雪音邂逅之時,雪音奶奶便努力爬上一棵桃樹,希望千鶴幫忙搖樹讓樹上的桃子落地,這個場景牽動著雪音的童年記憶,移民日本的歲月,她曾頑皮地爬上一顆鄰居富人家的桃樹偷桃,忽然鄰居家的女兒開門,兩人對望,她緊張地搖動,一顆大桃子掉落水面,開始漂流,她急忙逃離,沒想到桃子卻緊跟在後,最後撿起桃子與哥哥分食,裡面竟然潰爛生蟲。旋即,敲門聲響起,原來是鄰居的女兒,一身好看典雅的和服,帶著一籃豐美的桃子前來分享。這是日本童年的美好記憶。但是,對日本的歷史記憶是複雜的,如同雪音面對櫻花的一再投射,雪音終於忍不住說了,「櫻花下埋了屍體,吸收屍體的營養,才開的很美,家人就埋在櫻花下」【1】。
濱邊風運用《桃太郎》的精彩之處,在於她重建了日本時期日文老師以《桃太郎》的故事,教授台灣小孩日文的場景,其中一個台灣孩子舉手發問:「老師(せんせい),桃太郎被老奶奶撿起之前,是哪國人?」這個天真無邪的童言童語,個人以為是全劇的核心,透過質問這個傳說,濱邊風似乎想問的是,在國家統治政治收編我們的認同之前,我們能否回溯生命長河的上游,找回自己的生命,定義自己的認同?又或者,如果認同只能一再被政治暴力所裹脅,我們能如何成為自己?
雪音與千夜後來成為莫逆之交,他們對彼此的局外人邊緣身分惺惺相惜,最後一起搬到大阪,在那裏重建生活。在大阪的百貨公司上班,雪音又再度遭遇身分認同的質疑,一個台灣旅客因為雪音不會說閩南語而拒絕稱說她是台灣人,千夜氣憤地用流利的台語回應:「你沒有權利決定我們是誰!」雪音為了照顧父親,終究回到了台灣度過餘生,而千夜嫁了個日本丈夫,落地大阪。
歷史暴力遺留的問題,具體而微地展現在當代的生活此刻。濱邊風對日本帝國殖民遺留下的歷史問題觀察敏銳,在鋪排這些人物的關係處境之時,她把政治統治邏輯下造成的認同慾望與歧視邏輯,透過生活場景展現地一覽無遺。

上游(九條劇濱邊風提供)
後殖民時代的反覆辯證
《上游》的人物塑造與文學、歌謠意象的使用所占篇幅過大,讓寫實性細節有點無法支撐故事的合理性;各種錯認巧合的安排痕跡鮮明,用以一再強化認同政治邏輯下的投射與內化議題,尤其當劇末我們赫然發現,原來敘事者千鶴就是千夜的孫女!她來台灣不只為了學習中文,更是替奶奶踏上尋根之路,回訪從未現身的台灣父親。
還是不得不佩服濱邊風以素人之姿,又說又唱又演,單人完成了這個動人的劇本,劇本再巧合也沒有當天巧合,當濱邊風唸到千鶴即將對雪音表露身分之時,屋外忽然大雨,劇中的午後雷雨巧妙地來到讀劇表演的時空現實,彷彿雪音與千鶴就與我們一同坐在這個沒有空調的塌塌米空間裡。
演出後,不少廈門教會的長者在席間用日語熱烈地交談,細數這裡曾經是日本時代的哪裡,哪個灣生阿嬤來台灣申請出生證明,彷彿日本時代不是記憶而是此刻。而《上游》劇本裡透過情緒營造,試圖打開對認同邏輯的批判思索空間,瞬間化成了濃濃的鄉愁與感傷,意識形態與情感的辯證,從戲裡到戲外持續在後殖民台灣的此刻,反覆無間地辯證著。
註解:
雪音透過這句話提醒櫻花一昧浪漫化日本,忽視了日本帝國暴力的問題。編劇也在敘述桃太郎故事時,強化了桃太郎去攻打鬼島的敘事,闡明這個前民俗故事,在台灣日殖教育下,作為思想武器的意義。
《上游》
演出|九條劇 濱邊風
時間|2022/06/26 14:30
地點|臺灣文學基地悅讀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