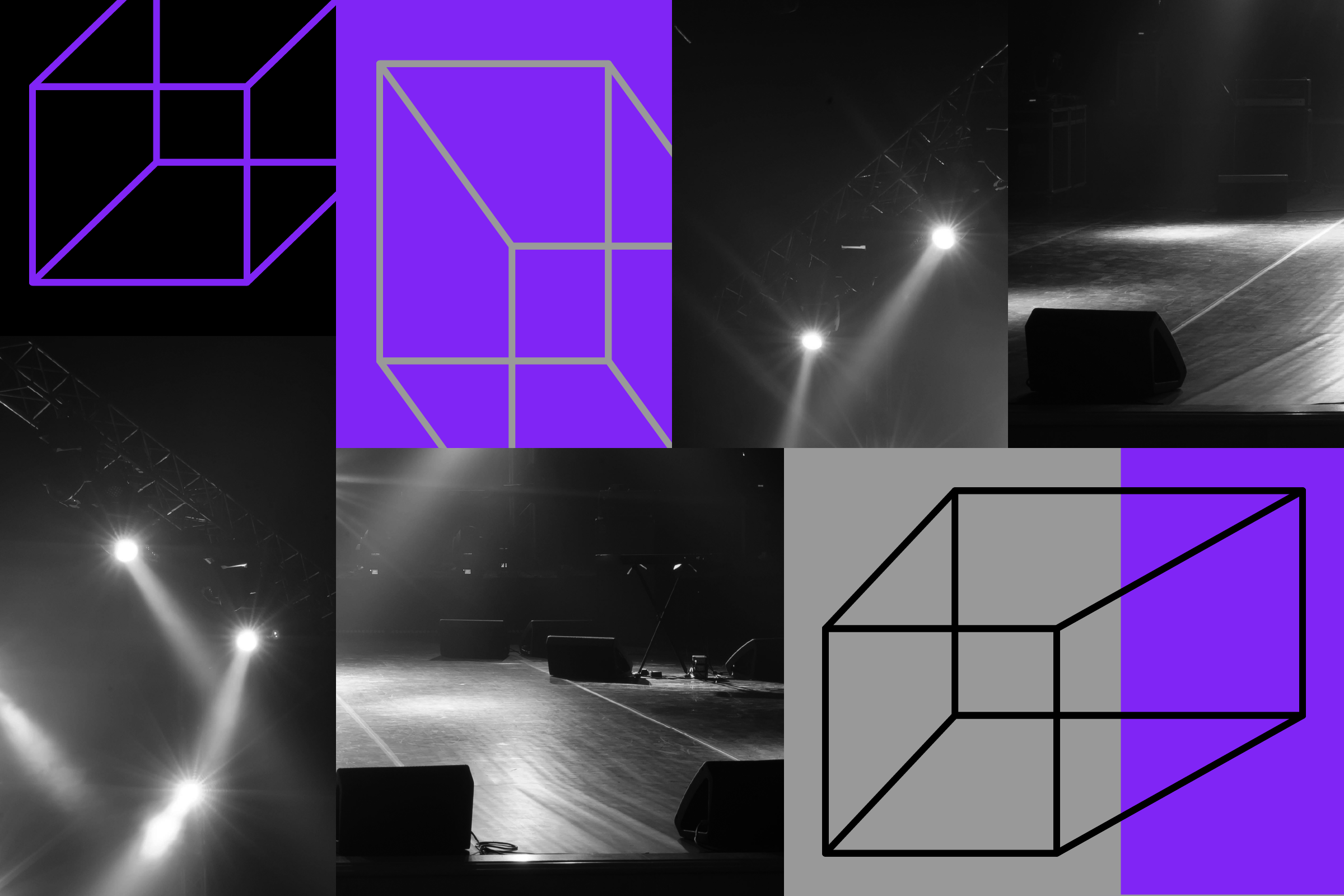
文 彭梓宜(臺灣藝術大學舞蹈學系碩士班學生)
碧娜・鮑許基金會(Pina Bausch Foundation)首度於亞洲正式授權《春之祭》演出版權,由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學院演繹、重現經典,排練指導為烏帕塔舞蹈劇場 (Wuppertal Tanztheater)資深核心舞者余采芩,與四位碧娜鮑許生前親授的舞者們共同傳授和重建作品。
土壤,象徵著生成與孕育,體會溫暖及繁殖希望的存在。但在《春之祭》舞台上的土壤則如同印記,更多的糾結或渴望埋藏之念想,凡走過,土裡與身上都會留下痕跡。因此比起土壤,筆者更傾向將其解釋為「泥土」,帶有佔據、無法輕易擺脫和割捨的想像。
作品的開始,女舞者拿著一塊紅布奔跑,接著趴於紅布和土壤之上,用全身感受它們的柔軟、細膩。接連出現多位女舞者以不同的形式出場,不變的皆是對大地的敬畏、崇拜,多次出現雙手由上至下抹過臉龐的動作,傳遞著祈禱與渴求之意象,舞者持續奔跑,只見趴於地面的女舞者緩緩地捧起紅布,示意著少女們即將面臨一場血光獻祭之禮。
《春之祭》的靈感源自於俄羅斯人對於祭典的想像,一群異教徒的長老,要求一位少女跳舞直至死亡,奉獻生命祭祀春神的過程。對大地越是敬畏,恐懼便越發深刻,女舞者整齊劃一地顫抖身體,雙手緊握、伸直手臂、大力揮動的動作貫穿整首舞作,直線性的肢體線路也讀出舞者毫不猶豫、迫切的情緒。
男女舞者交錯圍成一圈,緩緩進入挑選少女祭品的儀式,面向圓心舞者們招喚著春神降臨,背對圓圈像是守護著這股神秘能量,而排隊般的望向前一位舞者時,女舞者依偎在男舞者身後,則顯現出傳統下的萬般無奈與不捨,土壤吞噬的不僅是少女的生命,更是人心的善良與憐憫之情。
女舞者一個個著急忙慌接過紅布,強烈的音樂堆疊與惴惴不安的神態,在這一刻交織得特別濃烈,獻祭少女顫抖換上紅衣的過程中,男女舞者兩兩一組,劇烈地展示著雙人舞技巧:女舞者跨坐於男舞者的腰部、跳至男舞者的肩上⋯⋯將畫面營造得更加暴力與衝突,好似在闡述獻祭少女內心的絕望與崩塌,男舞者將獻祭少女推至前方,獻祭少女由驚嚇而無法動彈,一直到頓悟並接受宿命狂舞至死。整個過程筆者也隨著舞者的情緒忽上忽下,透過少女的殞落,反思1975年的社會現況與處境,並道出編舞家碧娜・鮑許在《春之祭》中蘊藏的階級、性別、種族議題。
下半場播映著碧娜・鮑許編創當時的紀錄片,看見她對舞者由內而外的高度重視,先有原因再來處理外型,因為有她堅守《春之祭》的故事精神,才有今日於台上精彩重現的經典作品。
泥土包裹著身軀是舞者努力抗衡與訴說的印記,平鋪於舞台的土壤交織、夾雜著恐懼、淚水、汗水和盼望,北藝大舞蹈學院所演繹的《春之祭》展現了少男少女的稚嫩,和對傳統毫不質疑的信念,強而有力又精準扎實的肢體展現,替時代劃出一道嶄新的樣貌、讓經典保存得更加璀璨與深刻。
《春之祭》
演出|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學院
時間|2025/01/04 15:00
地點|臺中國家歌劇院 中劇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