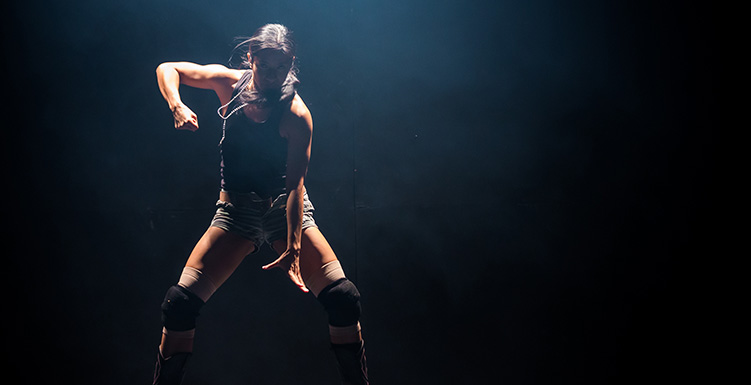
Eisa Jocson的《身體計畫》已有不少人闡述其性別意識與操演,這篇主要做的是補遺,其一是Macho Dance裡音樂的時代性,其二則是詢問作品Corponomy如何透過回顧與現場性、形成論述,最後則是獨立藝術家帶著作品移動的策略。
在台北藝術節,《身體計畫》歸屬於「共想吧」之中,開宗明義,思考、討論、溝通,是「共想吧」的要點。以《身體計畫》來說,除了演出,也包含了工作坊與創作對談。當然,有工作坊與創作對談並不意味著作品有著強大的論述能力,畢竟任何作品都有可能有工作坊與創作對談。在此我主要還是把作品被擺在「共想吧」視為一個小小的指標,細看「共想吧」,其節目的挑選與相應內容的操作,存在著溝通或者論述議題的渴望,而我認為《身體計畫》也提供了許多思考的空間,且作品本身就有著論述的企圖。
以Macho Dance在台北演出的操作為例,如果對比Corponomy影片中Macho Dance使用的音樂,其實有相當大的時代差異。台北場的音樂,幾乎完全著重在軟調性的芭樂情歌,以及陽剛的搖滾樂,但其實透過Corponomy的影片,看見的Macho Dance,還包含了嘻哈、電子音樂等等樂種。在台北場Macho Dance的音樂裡,恍惚間會感受到類似台灣美軍俱樂部可能有的氣氛,大量可翻唱的英文歌,也很像是雙城街的老派Pub會出現的橋段。在冷戰架構下,美軍駐軍與當地流行文化的關聯,其交纏似乎恍然可見。刻意選擇老派芭樂歌與搖滾樂,為作品定錨了運用音樂向前回溯的時間點,當然,這是一種全球化的狀態,但更多的,我認為也暗示了展示男性氣概中的特定幻想與時代性裡的政治意義。
從音樂的差異去強化與理解的政治性,牽涉了作品發展的時間性,這正好也是Corponomy讓我感到相當滿足的地方。在Corponomy當中選擇的作品,除了線性的敘述與作品本身的影像紀錄,也包含了Eisa Jocson的學習歷程與田野紀錄,對於「文字性」的論述,或許在演出中稍微粗糙地直接以文字傳達,然而影像的編年與檔案播放的方式,是相當有意識地回應著文字的論述。例如鋼管舞中爬上公共空間的旗竿,其對公共空間的侵襲,配合著文字更有著力點。與此同時,Eisa Jocson應該也深深了解作為表演者的自己,是她擁有的最大武器,在影像的輪番/並時播放中,她在現場選擇的動作與節拍,並置了此刻的時間與當時的紀錄,於是並置一方面是影像性的,例如不同的Macho Dance學習過程,另方面也是時間性的,是此時此刻的Eisa Jocson對當時的身體的回應、補遺、附註。
以身體回應身體,以身體的回應來製造論述,我認為是這個作品最有潛力也最深思的部分。從文字開始,進入影像的邏輯與身體的回應,再慢慢導至現場的演出、互動、嘲諷,觀眾一方面觀看藝術家線性的成長與變化,一方面透過現場的身體去理解前作與後作之間可能的連續性,以及藝術家在摸索過程中逐漸拋棄的(至少,不打算在這個演出中呈現的)。例如對公共空間的侵襲從鋼管舞後就消失了,然而學習舞蹈的身體,以及轉化空間與象徵的創作增多,都是例子。
Corponomy的影像紀錄對於現場觀眾而言,也是較為方便(理解)的媒介,對時間與行動有種仿若在場的想像,又或者多了幾分(虛構的)「真實性」,尤其是攝影機的畫質粗糙時。縱使攝影機的視角永遠有限制,且視覺僅只是感官的其中一種,在影像紀錄、創作交錯播放、現場身體三者之間,不同層次的視覺內涵,確實有彼此對話的空隙。
這個空隙是什麼?我覺得還是來自肉體活生生在場的Eisa Jocson。是她身體的此時此刻,讓過往有了一個相對的位置。也因為現場身體對過往身體的回應與重現,讓她作品的關懷核心得以浮現,不管是國族、身體、節奏、文化意義上的核心,都鎖在她的身體之上。從解釋性的文字過渡到表演性的語言,身體與影像的互動關係逐漸過渡到現場的身體,這對我而言相當令人振奮。這個過渡的過程,說明了表演及紀錄之間,不一定需要長篇大論的語言,觀眾也可以試著理解演出者的身體知識如何成就為此時此刻,而這身體知識的展現與回顧,也是論述的一種。
最後,這兩個作品都有些小地方值得獨立藝術家參考,其一是兩個作品舞台設計上的刻意簡單,這讓移地發表的可能性大大增高。其二是媒介的可親程度,在Corponomy的影像轉換上,只需要最低技術的螢幕動態擷取,就可以一小部分地讓觀眾從創作者的角度去看見影像。一台筆電在手,身體準備好時,都可以依著不同地點而微調Corponomy的呈現內容。媒介的技術程度降低,作品的完整度仍然足夠,孤軍奮戰時,把形式想簡單些,或許作品本身的意義更能清晰浮現。但當然,一切還是需要創作者清晰的思考,Eisa Jocson對身體的現場性,以及身體的現場性能勾引出什麼困惑、愉悅或思考,有一套自己敘述的脈絡,讓智識與心智的構成不至於阻斷現場的氣氛,這非常難得。
《身體計畫》
演出|Eisa Jocson
時間|2018/08/09 19:30
地點|水源劇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