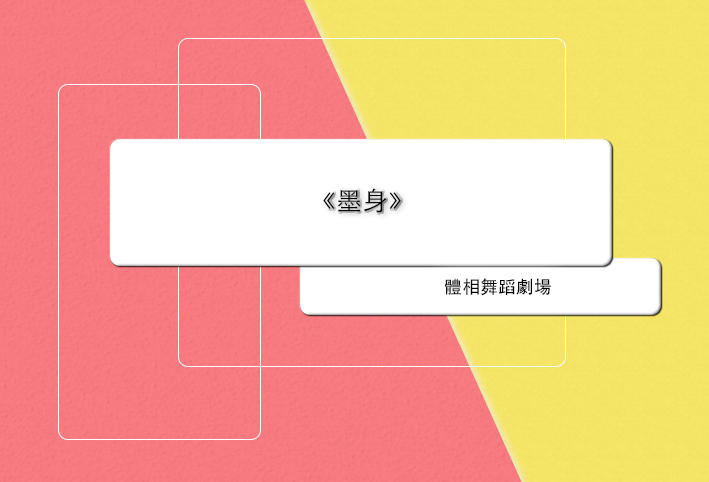
朱蕙琳(臺灣藝術大學舞蹈系在職碩士研究生)
墨染上身是世間
《墨身》以水墨藝術概念融入創作當中,運用色彩的對比特質,將蒼白與墨黑相互依偎交疊、拉扯、顫抖、分離、輪迴,如同我們曾經所遺忘退去的情感樣貌,為「體相舞蹈劇場」哲思系列作品之一。
隨著時間的變化將不斷退去的色彩、形變的樣貌,藉由舞者肢體繪畫出人與環境之間的思維互動,審視生命中最深層的記憶與情感,透過對於舞蹈的想像及共鳴,達到與創作者生命經驗與群體關係之間的連結,進而轉化為生命的本質,與觀眾自身的生活經驗相互呼應。
墨的變化
初始在若有似無的音樂中,只見些許微光投射在身穿白衣的舞者,引領著觀眾進入到舞台裡的世界,舞者緩慢且平穩地行走著,霎時間身旁的舞者以多變的舞步在舞台間來回穿梭移動,台上的舞者自顧自地跳著屬於自己的舞,宛如現代人之間的冷漠情緒,但看似疏離,卻因各種交錯串連影響著彼此。從眼前動與靜之間的交互流動,營造出時光流逝的意象,身旁擦身而過的人都是生命中的過客,唯一不變的是不斷成長的自己。而後獨舞者緩緩離場,燈光下的群舞者慢慢匯集在光圈之中,透過舞者的肢體堆疊,不斷連綿交錯移動、相互依賴、扭曲纏繞、時而緩慢、時而緊湊,舞者有如鎖鏈環環相扣,發展成共同姿態的多人舞蹈組合,藉由舞蹈空間轉換、重複、翻轉,變化出各種多樣組合及樣貌,象徵生命當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短暫且不斷的流動變化。
該作品其中一個場景所安排情境,在周遭飄逝而過的舞者慢慢消逝分散,將一縷燈光聚焦在一位身穿白衣、手持一把似毛筆又似拖把的舞者身上,這位舞者不斷運用手上的道具,想盡辦法抹去擦掉一些無形的痕跡,暗喻著我們每個人的生命經驗及過程,無論好與壞都無法抹去,看似平凡簡單的物件,結合起來卻又錯綜複雜,提供觀者對於「墨」與「抹」兩詞之間與舞作關係,令筆者對於「墨」有了新的思考面向。
何謂白?何謂黑?
當燈光再次亮起時,一群身穿白衣的小舞者,從舞台後方平行並排進入於舞台中,動作中透漏著對未來的期盼,自由的向天空延伸小巧的手腳,呈現了純粹、單純、以及對夢想的憧憬,猶如一幅純淨的水墨畫,少了塵囂的紛擾,只留住了心中無瑕的美好。
隨後音樂的轉換鼓聲響起,舞者藉由強烈搖擺抖動著身軀,將揮動的手臂拋向空中帶動肢體翻轉,腳步時而跳躍輕快,時而步履沉重,表達出人們心中的壓抑,同時又像是在掙脫無形的束縛,多層次的複雜情緒與先前的小舞者形成強烈的對比,彷彿暗指夢想與現實的掙扎及取捨,與兩者的相互連結及關係,延伸值得反思的「難道夢想與現實是無法共存的嗎?」。
白亦是黑,黑亦是白
舞者的表演中,無論是肢體技巧跟情感展現皆在水準之上,在獨舞與群舞中讓情緒與肢體呈現為一體,淋漓盡致得表現出「以身體為墨,轉化為墨性的身體揮灑。」
在舞作的畫面呈現,運用白與黑做出視覺色彩上的強烈對比,將舞者代表的意義作出明顯的區分,從服裝色彩上白轉換為黑,最後再從黑回到了白色,當中意義也值得我們細細回味。
筆者認為,身在科技變化快速的時代裡,我們何時能夠放慢腳步去審視自身過往的生活經歷,透過「體相舞蹈劇場」哲思系列作品,能讓觀者與創作者在無形中連結彼此之間的關係,使我們對於思考及創意有很大的共鳴及激盪。藉由《墨身》對於黑白之間的定義,暗指我們對於人、事、物都有著先入為主的思維,將我們所遭遇的事情分別成「好」與「壞」,就如同想要抹去身上的墨,但無論怎麼擦拭,都無法除去過往留下的痕跡,反之,如果都抱持著感恩的心去面對,才能真正的「生存如抹,落盡繁花,泰然自若」。
不禁期待未來對於有同一方向的創作者能透過多樣化的表演形式,建構出一個思想溝通交流的平台,為觀眾們提供更多深層的感受體驗。
《墨身》
演出|體相舞蹈劇場
時間|2021/05/01 19:30
地點|新北市藝文中心演藝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