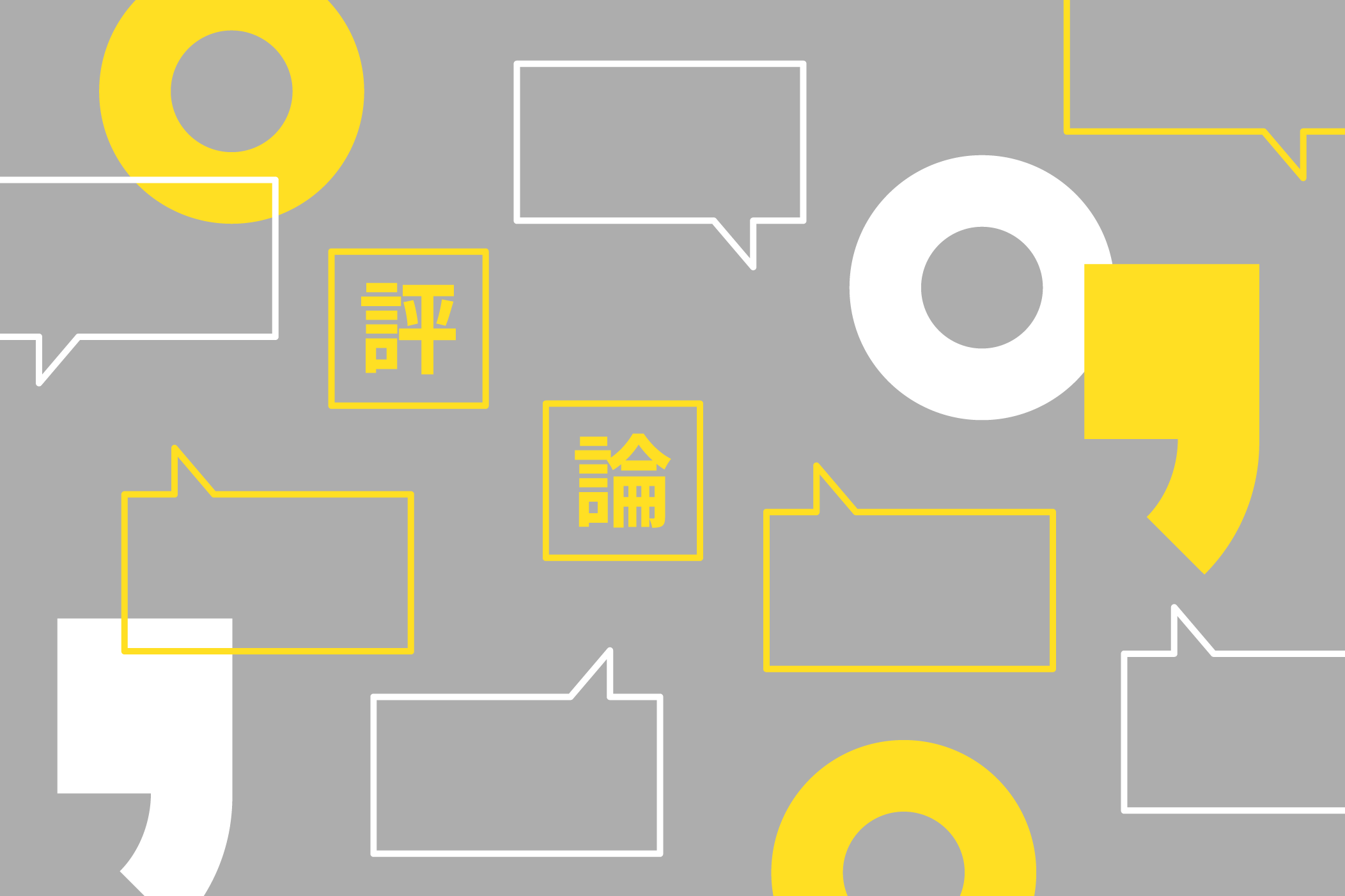
呂樾(台灣大學台文所博士生)
《肉身風景》是由 Meimage Dance 藝術總監何曉玫與數位藝術基金會共製的虛擬實境(VR)作品,並很大程度延續了《極相林》中對於「身體」的思考。可以說,《極相林》嘗試剝除了對於舞者的原本想像,使舞者藉甫演出開始時的儀式段落成為一組組肉身團塊,而此一由肌骨「強度」(intensity)而非「故事」敘事所組配的舞蹈演出,在很大程度上解消了「舞者(表意)」的連結,而是肌、骨、力量的持續流變(becoming)的無器官身體(OwB),並以此回歸到「極相」這個生態詞彙所指涉的「演替」本身。《肉身風景》則更進一步將「觀眾」加入上述提問,即「觀眾」能否,且又如何參與整體影像運動之中。
在《肉身風景》中,觀眾將置身於一個躺在無際灰色沙(山)丘中的巨人腹部,隨著巨人逐漸起身,觀眾的「觀看位置」也隨之移動,一路由右腳銜接至左腳、背部並「滑」上巨人的頭部,並且在最後(如果你願意的話)與巨人四目交接。整體而言,因為作品本身無明顯的敘事軸線,且扣除已被預設的移動路徑與巨人起身姿勢,在移動的過程中觀眾可自由選擇欲觀看的方位,是以不同的觀眾將擁有不同的體驗。重要且與《極相林》類似的是,因為觀察對象(巨人)的體積過於龐大而觀眾視野有限,除了少數時機,觀眾不太有機會見到巨人的整體形象,而只能看到某些巨大而無法掌握的灰色塊體在眼前揮舞,甚至因為周遭環境均為灰階色調,也模糊化了巨人與風景的界線,巨人因而成為地景的一部份。我認為,此處的問題或許不再是「舞蹈作品」的「意義」為何,或是否能「再現」或「傳達」某種由身體的藝術形式帶來的共感(尤其本作仍被視為舞蹈作品的「VR版本」),而是觀眾的視覺經驗與體感經驗如何、與能否參與作品的運動?
首先,因為《肉身風景》雖多次將觀者推挪至「立足點狹窄」的身體部位(如:膝蓋、頭頂),以至於視覺上認為自己即將墜落,但由於缺乏如具體的「突發驚嚇」或「墜落」等VR作品中常見的視覺驚嚇,觀影時的帶入感並不能說強烈。另外,雖有賴於呼吸音效的強大與起伏的巨人肚皮,加劇了巨人「鮮活肉體」的意象。但也因為此處的強烈「擬真」,更迫使觀眾意識到,其腳踏的並非柔軟且在起伏的軀體,而是堅實的地板。再者,觀者移動時僅能以「滑行」,而非「行走」的物理擺動。是以,即使觀者隨著巨人身體不斷運動,但觀感依舊弔詭地卡在靜態的景框(film)觀看與動態的「參與影像運動」之間。
在此提及觀影的尷尬並非要指責《肉身風景》不夠「真實」,或指出現有技術的限制。如同王柏偉所述,所謂的VR(virtual reality),有別於紀傑克提到的「虛擬現實」,並不指涉網路空間的「整體」想像,因該思考預設了「整體」之外尚有一個處於離線(off-line)的現實,且其中還有一個「觀察者」以指稱「網路空間」。相對的,在VR中「藉由『沉浸-互動』技術的幫助,多個平行世界得以同時出現,因而在「虛擬實境」中,世界之於觀察者的關係,從『再現』變成『呈現』(prasentieren),而觀察者與平行世界的關係,不再是「虛構性現實」,而是「虛構就是現實」(reality of fiction)」【1】。是以,上述視覺與體感經驗的斷裂並非意味著「現實物理世界」的不斷現身,而同為「『肉身風景』世界的一部份」,由此可見,將詮釋導向作品的不足並不具意義,而應一併納入其世界觀之中。但若將觀影時的弔詭體驗也視為作品的一部份,則此一在之間(in-between)的不協調又意味著什麼?
我認為,與其說何曉玫試圖藉「沉浸-互動」技術解消「舞者」與「觀眾」間界線,並使觀眾「體驗到精神化的地景,進而實踐《極相林》舞作編創時,對生命的想像、痛、以及身體共感」【2】倒不如說《肉身風景》中身體與視覺的反覆斷裂與不協調,既強調了「我(作為觀眾)」在場,也提問了在「VR」與「舞蹈」的脈絡中,觀眾如何被賦予能動性。在觀「舞」時,不只觀眾無法一窺舞者全貌,舞者甚至成為了地景意象(Image)與肢體殘塊,我們是否還能清楚指稱「舞者」作為生產意義的主動者?而在VR中,攝影機的視角與不協調的視覺/身體感不斷逼迫觀眾在靜態的景框(film)式觀看與動態的「參與影像運動」之間來回移動,每一次的移動與不協調都前景、並問題化了「觀眾」的觀看位置。當不管視覺或身體的體驗永遠都如此斷裂而艱鉅,觀眾永遠都只能依據地景的配置尋找對自身最有利的閱讀「姿勢」,不管是物理上的蹲在地面觀影,或是形而上的作品詮釋配置,在這個意義上,「觀眾」得以被作品「賦權」。若說《極相林》透過以肌、骨拼裝出的臨時器官拒絕了一個統一整體的舞者「形象」;《肉身風景》則進一步挑戰了「舞者(表意)-觀眾(接收)」的分工等式。舞作中,在使「舞者」成為地景的同時,「我」作為一個怪異的參與者,一個在巨人的平行世界裡格格不入的幽靈,反過來在身體感上被賦予了主動參與/不參與、詮釋/不詮釋的自主權,變相的破壞了觀眾往往作為接收者、被同感者的被動立場。
註釋:
1、王柏偉〈VR與形塑世界的三種模態〉,《藝術松》,1期,(2020,11),頁13。
2、參見《肉身風景》展覽介紹(https://dac.tw/from-flesh-and-blood-to-virtuality/)
《肉身風景》
演出|何曉玫舞團、在地實驗
時間|2021/12/10 17:00
地點|台灣數位藝術中心
你可能還想知道:
《肉身風景》為2021新舞臺藝術節X數位藝術基金會─《肉身到虛擬:極相林VR展》其中一件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