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顏采騰(專案評論人)
作為 2022 新點子實驗場壓軸的《聲妖錄》,雖然日前意外被批評為「公然交鬼行邪術做法」,但它其實沒有一絲恐怖嚇人的物件或音效,更沒有什麼招妖儀式。相反地,它平實地探索日常聲響,重新打開人們的聽覺感受,是件可親可愛的作品。
一場大型的聽覺猜謎
《聲妖錄》的定調是一場「遊走式展演」。除了如字面所示,觀眾能在劇場內行走之外,它還多了點沈浸式劇場的意涵。在我們等待上樓時,一位蒙面黑衣人現身引路,並在電梯間播放了以下錄音:「歡迎光臨國家聲妖院。⋯⋯請勿攝影、使用陽間語彙⋯⋯。」上樓之後發現,前臺也被佈置了一番,原先的「Experimental Theater」字樣被稍加覆蓋,變成了「Experimentally Hear」【1】。
走入昏暗的劇場,我們隨著腳步先後看了三組日常行為的展示:燒開水與烤吐司(演員身處半透明的簾幕中,帶了幾分神秘感)、對坐的二人傳訊息按讚(並屢屢把讚按爆;桌下的雙腳彼此逗弄著)、把玩鐵架以及生活物品;看似平凡,卻又隱約散發著韻律性及秩序感,給人非常微妙的體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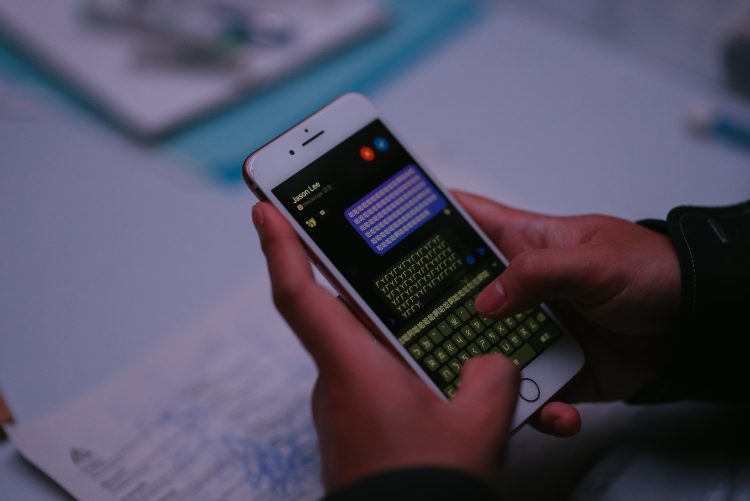
聲妖錄(國家兩廳院提供/攝影唐健哲)

聲妖錄(國家兩廳院提供/攝影唐健哲)
之後,我們被引導到空間中央的座位區。座席為兩側對坐,略呈放射狀,周圍則被一大圈半透明簾幕圍住,簾幕外的一切模糊難見。不久後,各種聲響開始從四面八方現「聲」,有時是演員以各種方式使用物品,有時是裝置的合成聲響與聲景。例如,地面四方傳來渾厚的共鳴,那是大鑼與平底鍋的拖曳聲響(也許再加上了合成的擴音);或者,具阻力的摩擦聲自遠方漸漸逼近,原來是演員將椅腳套上鞋子,在地上磨蹭而來。此外,演員也在中央觀眾區域來回穿梭,並同時揉紙、運球、穿高跟鞋用力踏步、匍匐蹭地、丟乒乓球、撕毀布幕、撒落碎石、滾電池⋯⋯等,幾乎無奇不有,卻又無一不平凡。在低光源與簾幕的阻擋下,我們的視覺功能幾乎失效,於是只能豎起雙耳,絞盡腦汁猜測聲音是哪裡/如何來,形同一場大型的聽覺猜謎。
最後,隨著演出進行,布幕逐漸塌落,我們得以看見劇場空間的全貌,而出口在此時敞開,光線照射進來,演出結束。
藝術源自改變聆聽的方式:場域與方法
講到這邊,有幾個問題顯得非常重要。例如:這些平凡到不行的日常聲響,能稱得上是音樂或聲音藝術嗎?演員的各種尋常行為展示及物品使用,能算是演奏嗎?進一步地問,刻意策動如此大量日常聲響的意義何在?若要找到答案,我們必須回頭叩問作品的「形式」——亦即,這些日常聲響被組織、被呈現、最後被聆聽的場域與方法。
回想前半部分的「遊走式」設計,以及後半部的圍繞式演出,它們都有一個明確的功能:營造多焦點的、去中心化的劇場體驗。傳統意義下的劇場演出,是平面鏡框的、追蹤式的體驗;聽眾的專注力總追著某個特定的演員或聲響,其體驗因此是單焦點且中心化的。而在《聲妖錄》這端,「遊走」意味著視角的自由,我們可以極遠或極近地觀看這些日常行為,並無對錯好壞之分;而演員圍繞且四處穿梭的演出方式,則讓每個位子都有獨特的聲響體驗,不再有「好位」、「爛位」的問題,觀眾的體驗也因而是去中心、多焦點的。

聲妖錄(國家兩廳院提供/攝影唐健哲)
另一點,是聲響的陌生化效果。前面提到,少了視覺的形象導引,要將雜多的聲響表象轉換成概念其實非常困難,於是原先能直觀體會的碎石聲、滾電池聲都變得相當抽象(說實話,到燈亮前我還真沒猜到);同時,藉由日常聲響的大量轟炸,原本熟悉的聲音似乎也漸漸變得陌生,最後逼得我們只能直觀地、純粹地聆聽聲響本身。
最終,這些設計都導向一個目標:改變人們對於日常事物的聆聽方式。回想起「國家聲妖院」、「Experimentally Hear」等巧思,這些細節早已暗示我們,要以全新的方式感受周遭的一切事物,陌生者亦然,熟悉者亦然。平時,我們的聽覺總是自動自發又不帶反思——例如,我們聽見一段言語就立刻曉得其意涵,開車時聽到警笛鳴聲就緊張地讓路,看韓劇時聽到感人的配樂就跟著落淚。但是,我們有沒有辦法再退一步,回到聽覺經驗與概念、情感、行動連結之前的時刻?我們能不能更純粹地、樸實地、甚至是帶點反思性地感受聲音「本身」?
藉由這些反思,「感受聲音」本身化作一種積極的審美行動,日常聲響也因此不再日常,進而被昇華為藝術。或者,以演出的文眼「妖」作為比喻:若聽者稍加留心,便能發現聲妖無處不有,欲解其妖意,用心聆聽便是。
延續到劇場外頭的「妖聲」
若讀者曾留意節目單中的文字,便會發現《聲妖錄》非常鼓勵觀眾的積極參與:「觀眾可在參與演出的過程中,形塑出專屬自己的聲音妖怪,建構各種聲妖的奇想旅程。」這不只是聽覺與想像力意義上的積極,連行為動作也可以積極投入。在演出中,我看到演員將氣泡袋遞給鄰近的一位觀眾,示意她一起「妖」起來;而與我同排的一位小孩,也真的撿起了一顆乒乓球,加入製造彈跳聲的行列。我不會覺得那是干擾演出的舉止,反而是體現了《聲妖錄》積極打破劇場體驗範式的願景。

走出實驗劇場內部,大量的七彩塑膠袋包覆出口通道,連接至下樓的樓梯;而在樓梯間,仍見幾個黑衣演員敲擊扶手、運球、刮牆壁等,將「妖聲」一路延續至出口,也延伸到了外頭的世界。
離開時,我看見前方的一位觀眾,用手掠過一只只塑膠袋,一邊下樓梯一邊叩擊扶手及牆壁,陶醉在自己的聲妖宇宙裡頭。而我呢?我也跟著伸手輕拂塑膠袋,在樓梯間敲起扶手來了。
註釋:
- 老實說,當下我只發現了前臺佈置的改變,「Experimentally Hear」的細膩發現則來自本站評論人蔡孟凱的分享。詳見其粉絲專頁「劇場淚浮游」短評文章,網址:https://reurl.cc/g2XYl4。
《聲妖錄》
演出|洪于雯
時間|2022/06/26 14:30
地點|國家兩廳院實驗劇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