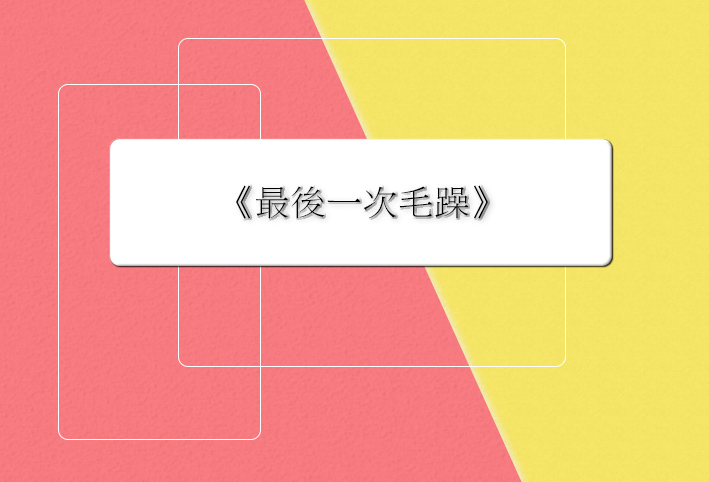
簡麟懿(01舞蹈藝術總監)
「⋯⋯見微以知萌,見端以知末⋯⋯」——《韓非子·說林上》
《最後一次毛躁》作為一場畢業製作的大標題,不僅僅是畫下學生舞者們在校園期末的總結,同時也是在為一共十一支的新銳作品打個比方,形容此階段的一種心理狀態——焦慮,然而觀眾並不能以此標題作為線索,用來觀看所有作品的敘事內容,這也是台灣舞蹈教育一貫通行的策略方針:中庸,有容乃大,故形成了特殊的學院現象,每年都能有大量的作品被產出。
在如此中性且通用的前提之下,創作之於學生舞者們,還是具有一個短時間明確且有企圖的方向性:在於建立編舞家自我的獨樹一格,故我們在觀看學生作品時,或許會認為「學生」作品難免停留在一個創作初期的淺層,但其實他們同時也在構築自己對於舞蹈美學的深度。
筆者在觀看的時候也嘗試避免落入這樣的印象之中,基於一場參加Gala【1】的期待感,去閱讀每一位創作者想要釋出的訊息,最終在兩個半小時的演出中,獲得的部分感受與疑惑如下:創作識別度,我們必須告訴他們我們是誰,這樣我們才不會淹沒在不是我們的他們之中。
《最後一次毛躁》沒有文本,其囊括了現代芭蕾、古典芭蕾、當代舞蹈、中國舞、舞蹈劇場等不同風格,筆者認為這顯示了藝術總
伯樂相馬;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
筆者認為台灣的舞蹈教育,或者是時候重新思考畢業製作之於新銳舞者的執行目標?作為壓軸的《千禧前夕—我們被製造》是由特邀編舞家董怡芬所發表的新作,同樣有趣而深刻的想法,董怡芬擁有更多的時間長度可以去深化自己的作品,普普藝術的風格相較於其同系列作品《搖晃的自由》來說,董怡芬在此次加入了兩重概念的鋪成,一是馬戲跳繩的多方運用,建立了一種簡單而強力的身體視覺,二是屬於年輕人話語的時代議題,透過文字的編排傳遞了作品背後的聲音,只是這樣的成果,不僅是因為董怡芬個人的經驗與天賦而成,同時也因為此作品擁有更多的時間可以鋪述,比起新銳作品中的《之下》、《紅消》,後者的完整性則受到長度的限制,在一個極快的身體表達過後就戛然而止;以往學院的審舞制度不僅是端看學生的創作意願,同時也衡量學生的創作水平,在多重考量之下,有些人或許會獲得一支以上的作品發表權,筆者思考的是作為創作能力的被肯定,數量與種類的多寡是否真為大學畢業製作的優先前提,又或者作為一個跨越職業的橋樑,搭建起更具競爭的發表空間,是否可以更加淬煉新銳們更進一步的品質提升也未可知。
現實之於現實
學院的現實與社會的現實兩者,不能合併而語,只是近年來盛行的創作競賽與舞蹈節,事實上也有人數與時間相關等限制,新銳作品《流》、《愚論》,前者以長棍為意象,組織了身體的流變,後者以氣球為發展,建構了更多的敘事可能,在短短的時間裡,他們或許不是建立一種身體語彙,但卻也用清晰易懂的方式詮釋了一種氛圍,可以符合學院的需求,且跟未來的社會相與競爭,即便獲得了這樣的優勢,新銳創作者又是否能夠洞察自身的舞蹈美學,是否能如自己所期待地擁有「形狀」,又或者受到快時代的影響,不知不覺中被丟進了他人的模組裡頭,這也是值得被探討的課題。
台灣的舞蹈教育鼓勵表演、創作與多樣可能,筆者認為透過這所謂「最後一次」的機會,若能對於學生進行想法上的打磨,或許在日後不久的將來,我們更能期待舞蹈廣袤的可能發展,且見微知著,看見更無設限的發展趨勢,在舞蹈的草原裡生根發芽。
註釋
1、Gala為晚宴的意思,在舞蹈作品匯演中,多有Gala、Collection 等稱呼。
2、《La Esmeralda》中譯《鐘樓怪人》,為一齣三幕五景的經典芭蕾舞劇,創作者為Jules Perrot 。
《最後一次毛躁》
演出|臺灣藝術大學舞蹈學系日間學士班
時間|2021/03/13 19:30
地點|花蓮縣文化局演藝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