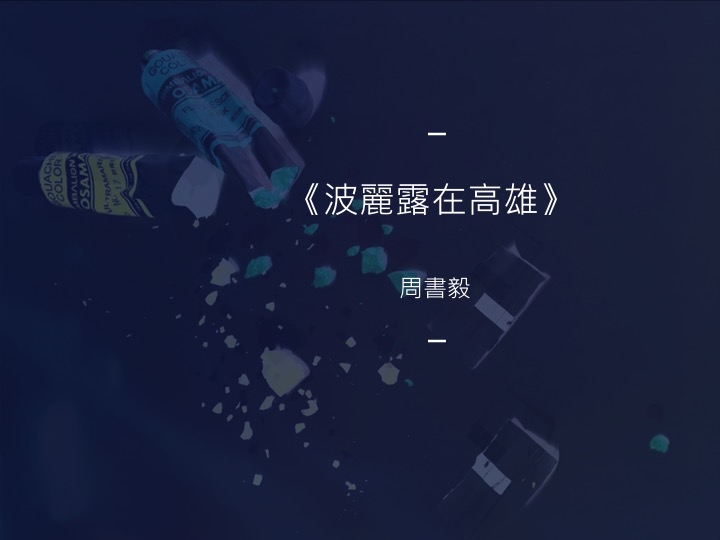
簡麟懿(專案評論人)
一個作品的生命究竟可以多久?雲門舞集的《紅樓夢》二十二歲後封箱,蘇威嘉《自由步》估計十歲就會完全長成,而《1875.拉威爾與波麗露》於2006年出生,2011年開始提著一只皮箱環島旅行,時至今日也有十六歲了。如果說每一個作品都是創作者從腹中懷胎十月而成的嶄新生命,那為何是此刻出現在高雄城市的角落裡頭?而改名為《波麗露在高雄》(以下簡稱「波」)的《1875.拉威爾與波麗露》,究竟又生成什麼樣子?畢竟其精神、結構以及成就,多數見證此作品誕生的觀眾們業已了然,如此一來「WHY-HOW-WHAT」就顯得相對重要。
《波》作為一個特定場域藝術(Site-specific Art),其特定的內容並非針對單一戶外平台,而是以作品所提供的概念與彈性空間為核心,針對複數場域,也就是「環境劇場」這個概念在進行表演,而筆者所觀看的下沉廣場版本,也與在2011年看見的板橋火車站版本有所不同。換而言之,《波》是一個會隨城市環境不同而蛻化的作品,這也是多數團隊在離開黑盒子劇場後,企圖在戶外空間尋找到的生命力,單就此點而言,《波》的輪廓與價值或許已經著實被確立,且難以抹滅也說不定。
為何而生?為何而作?
《波》是一首開心且神祕的小品,全長約三十分鐘,當工作人員在廣場周遭進行第一波宣傳時,火車站快速流動的人口結構,讓筆者自行捕捉到了比利時安特衛普中央車站的一場演出想像【1】,而作為一個城市記憶,舞蹈置入在眾人熟悉的環境裡頭,卻也有一種親密的陌生感,彷彿舞蹈從未來到過這個地方,又或者我們真的沒有在這個地方看過舞蹈。
然而事實上,自2020年高雄市文化局開啟「舞筵自然」起(後更名為「環境舞蹈」),後續積極喚醒各個場域舞蹈的可能時,舞蹈並不是真的觸不可及,而是在舞蹈的推廣上有許多不容易。
從筆者的觀察上看來,過去高雄較為大型的演出活動如《見城》、《船愛》等,比較是從活絡文化造景的角度出發,而「環境舞蹈系列節目」與此次《波》的演出,目的則比較偏向於喚醒舞蹈與民眾之間的關聯。不論是出自哪一個層面,雙方都須謹慎2011年林懷民對於《夢想家》的看法【2】,以及2022年邱坤良在觀賞《船愛》後的評論【3】。作為離開廟堂後的戶外演出,作品是否能帶來凝聚力,以致接下來《波》剩餘的二十六場演出,筆者認為是值得持續關注的。
當我們舞在一起
《波》的舞蹈結構,基本上由輕快的舞步、電風扇與雲霄飛車般的尖叫聲所組成;舞步自不用說,舞者透過疊加的動能與音樂性的張力相互結合,在每一次的「借力使力」中翩然起舞。而群舞的能量,有別於1961年莫里斯・貝嘉版本的慷慨激昂與加法的推疊,以及2019年董怡芬版本的自由奔放,與為了聚焦的遞減,周書毅版本更追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正如他過去的創作,細究人與城市的關係一樣。
其中舞者分作兩人一組的場景,筆者確實看見雙人舞的啟動並非先透過身體的拉鋸,也不是對拍對點的音樂配合,而是在雙方眼神的交互凝望後,進而獲得對方眼神回應的同時,兩位舞者才深吸一口氣,同步推動舞蹈的下一次進行,是極為有機且親密的雙人舞模式。
演出內容中,電風扇在2007年的版本是用於吹動地上的綠色碎屑,其顏色特徵為傳統藍白色電風扇的配置,而此次銀白色的選擇,似乎某種程度上降低了早期復古的視覺感,至於大量被使用的尖叫、嘻笑與無法被解讀的吼叫內容,也如同過去所帶來的幽默感般讓人頭皮發麻。
隨著作為楔子的音樂《布蘭詩歌》響起,到後來《波麗露》的進入,畫面的重複與人數的遞減,一方面形塑出這群人搭載雲霄飛車的畫面,一方面讓筆者回想起碧娜・鮑許(Pina Bausch)剛帶著《熱情馬祖卡》來台時的風潮,似乎都沒有人知道為什麼要這麼做,但大多數的人卻都想著「為什麼」?
林璟如的服裝是如此青春洋溢,讓舞者的聚集與行走所結構起的色彩美學,絲毫不遜於日前雲門舞集在國家戲劇院所發表的《霞》,但卻也不是偏向複雜的抽象線條,更非上述提到2019年董怡芬版本的運動風。
在林璟如的選擇裡,整體構圖更像是一種相較純粹的馬賽克彩繪,可以接納未來更多不同的城市風景或是編舞需求,其中有一幕是某位獨舞者頭戴安全帽,以奇異的視覺感滲入作品當中,卻也沒有破壞原本的視覺美學,這個過去不只一次出現在周書毅作品中的符號,以一個隱喻般的內容和不協調的姿態,輕微撥動場上的調色盤,色調上未必能融合作品的配置,幫助觀眾去解讀《波》的內容與氛圍,但可能還是要連結到我們所熟悉的城市印象,也就是觀察沿路風景時,那無可避免的行人與行車。
再生的城市,尋找舞蹈的力量
當與周書毅對話時,又或者接觸他作品如《Break & Break!無用之地》(2018)、《看得見的城市,看不見的人》等,都會從他的身上感受到一種流浪的氣質,而這份氣質尋覓著再生的能量,此後,倘若我們也將《阿忠與我》列入觀察,或許周書毅透過舞蹈所審視的,是一份生命的可見與不可見,不論是人也好,城市也罷,在看似凋零的事物背後,擁抱仍可觸及的各種可能,或許是給予他持續舞動的來源之一。
也因此,作為衛武營駐地藝術家的他,與衛武營一同推動《波》的企劃案,某個程度看來也是一種試探,試探高雄在地民眾對於城市本身是否熟悉?是否曾留意與觀察,而並非深入門道,也不是探看熱鬧,僅僅是擁抱一場生命的不期而遇,又或者進而追尋接下來十七場場域的足跡,完成一趟在地的微旅行。
至於大樹在哪裡?彌陀又是何方?猜想創作者本人也是這麼問著的。筆者作為高雄二十多年的居民,是否知曉他城的風貌更勝於在地的風景?而當生活的汲汲營營逐漸趨向麻木,《波》或許更像是《看見台灣》的齊柏林,讓人可以透過藝術家所擁有的視角,穿梭在即將,或正被隱性遺忘的各個區域。這樣的記憶呼喚或許會是無用的,然無用之用何所以?是為大用恐也未可知悉。
註解:
1、參考自Youtube頻道,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EYAUazLI9k
2、參考自公視新聞網,2011年陳姝君、彭耀祖台北報導,https://news.pts.org.tw/article/197214
3、參考自風傳媒「邱坤良專欄」,2022年,https://www.storm.mg/article/4207941?mode=whole
《波麗露在高雄》
演出|周書毅
時間|2022/04/24 17:00
地點|高雄火車站下沉廣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