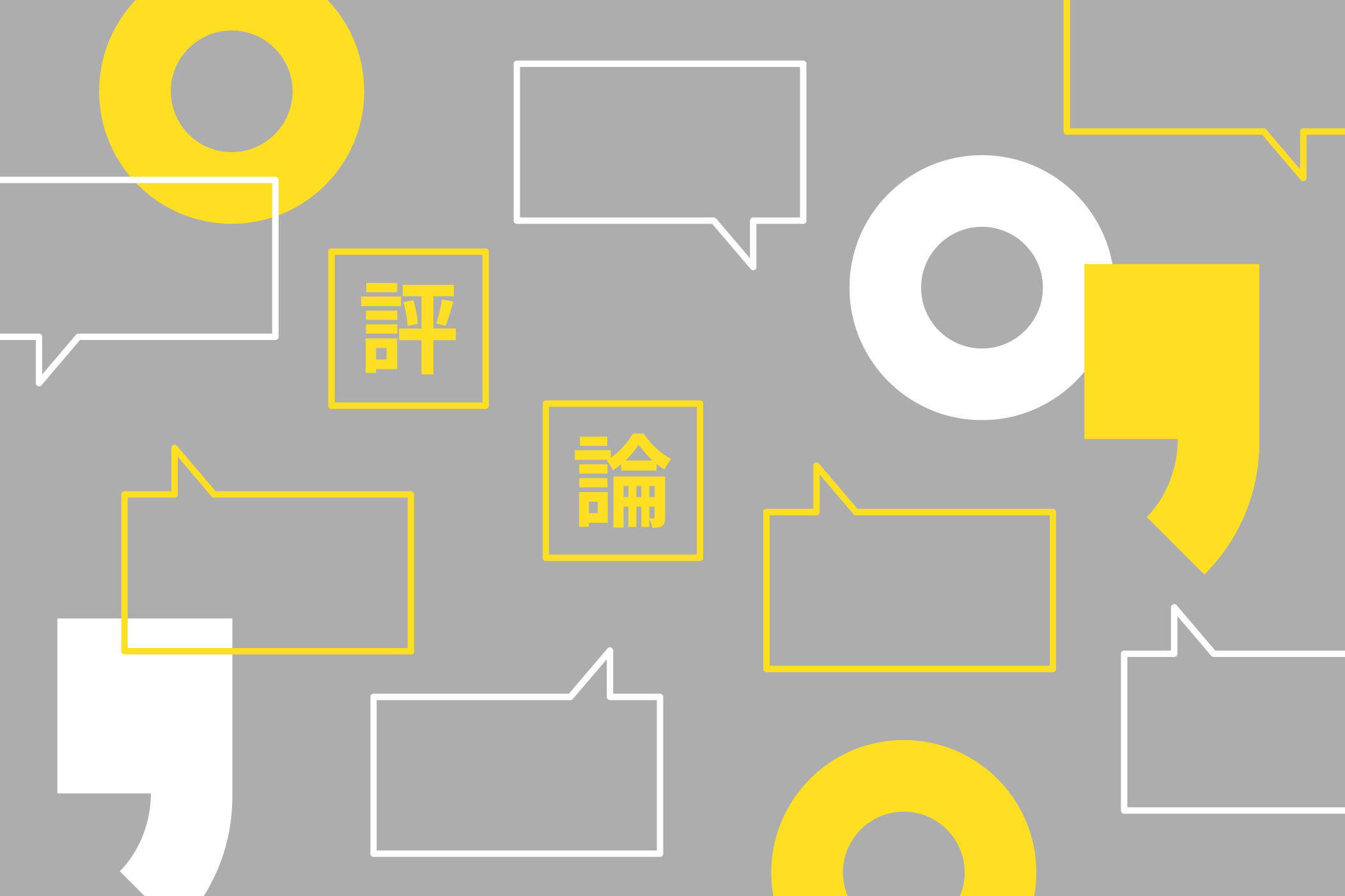
廖淑芳(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副教授)
「雞屎藤舞蹈劇團」是一個深耕台南的舞蹈劇團,由團長兼總監許春香從上世紀70年代自宅客廳兼舞蹈教室經營多年後脫胎孕育而生,至今已成立近二十年。「雞屎藤」是台灣原生種植物,單從這個舞蹈劇團以「雞屎藤」為名,便可以嗅到他們非但不排斥「臭賤」,甚至致力於歌詠草莽的強烈庶民性格。多年來他們以建立具府城人文感與庶民特色的臺灣民族舞為努力目標,除了演出的舞劇多以台南在地故事為元素,雞屎藤舞團的特質在總是以幾位舞者的簡約動作,概括與標誌所欲敘述事件的起承轉合,又以各自肢體的細微差異演繹其中人物情感的流轉變化。加上其常帶有民間戲曲特質的音樂、燈光、舞台設計等,不同於一般以對話為主的戲劇演出,「雞屎藤」的舞蹈劇往往或清晰優美,或震撼人心、總能擦撞出令人難以預期的感動與驚喜。而2021年12月18、19兩天在台南市文化中心原生劇場推出的《大事件─臺灣刁民林爽文》(以下均簡稱為《大事件》)便是一齣異常精采的大製作,與之前2020年便先完成的前導戲《誰是林爽文》的差異也值得加以比較。
以台灣史為背景的故事中,林爽文應是目前大部份人都聽過,對其歷史卻至今模糊不明並不真正熟悉的一位,因此也更有可以發揮的空間。之前在《誰是林爽文》前導戲中,整齣舞劇演出時間約一小時,全劇以舞者服裝的替換轉換今古,讓從漳州和平來到台灣彰化大里(今台中大里)的林爽文生平、另位領導人莊大田、道卡斯族女領袖金娘等眾多人物故事以舞者說講與動作變化的方式,被包含在現代年輕人的聊談之中帶出,使古今有著遙想呼應的對話。其呼應的是生活在當下年代的年輕人也有屬於他們各自的故事、各自的江湖。於是故事中包著故事,過去的大事件往往也是諸多小人物偶然撞擊與聚合而成,成就為此劇以「誰是林爽文」「江湖是什麼?」為整部前導劇的敘事核心。雖然限於舞蹈動作為主的抽象性,以及演出時間,林爽文事件能詮釋的幅度與深度有限,卻已經是一層次清晰,結構完整的好故事。
但如果說我們要來觀察如「林爽文事件」此一台灣三大民變之一的台灣史「大事件」如何在這齣新的舞劇《大事件》中被陳述?則比較從《誰是林爽文》到《大事件》兩齣可以各自獨立卻有著緊密繼承關係的劇有何變化差異,應可以更清楚了解,同時也可以看到兩齣劇在歷史敘事上的意義性。
首先相較於之前的《誰是林爽文》,可以發現《大事件》已經擴大為一個半小時的長劇,首先將林爽文出身定位為雖有其生卒年,知其里籍,但在所有漳州林氏宗親族譜上,卻都找不到他的家世族譜,彷彿這家人從沒存在過的迷團人物;又傳聞伊青少年時期大多在放牛與練武,而一則關於他跟牛走到哪,就有一隻大鳥飛到哪的傳說,更加深他的傳奇性。另外,從其情節結構:一、誰是林爽文?二、莊大田——天地會,三、Youtuber 愛林爽文,四、乾隆皇觀點,五、尪姨金娘觀點——Be Water,六、林爽文觀點——是實,七、江湖在哪裡?等七大場標題來看,更可以發現《大事件》除了保持「誰是林爽文」「江湖在哪裡」等前後兩個大架構外,基本上放大了同在天地會中的次要領導人莊大田、及女性領導人金娘等不同人物故事與觀點,還新加入了乾隆皇等滿清官方視角,而且林爽文真正現身了;同時也透過現代視角(主要透過一位對林爽文事件有專業研究的教授,及另位Youtuber的不同觀點)點出各觀點的差異性。也就是說新的《大事件》更著重在飽滿完整地呈現出包括官方與民間內部不同性別、階級、族群等不同視角觀點的林爽文事件。然而,表面上莊大田、金娘和林爽文的不同觀點卻都是在被綁縛、也就是可能非自願的情況下發聲,使這些陳述帶有一種反思性;而這位專業研究教授提出的「天地會」與「添弟會」及林爽文事件相關脈絡的說法,隨後又為另位 Youtuber 主張事件乃是漳泉械鬥另一體現,並批評「教授教授,會叫的野獸」的不同評價給削弱。換句話說,這部劇既藉由不同人物提出他們自己對林爽文事件的自我再現或他者詮釋,但這些再現或詮釋往往又被包納或呈現在一個不平衡的權力結構中,造成一種既建構又解構的現象。透過這些不同的評價與說法,本劇明顯試圖一方面呈現目前可見的林爽文事件之成因,過程、影響,也同時保留對此一事件各方認知和評價的困難與駁雜。從七個場次幾乎都以電視機畫面不穩時跳出的擦擦聲開頭來揭示其場次標題,就可以見到其嘗試交織多重雜音的創作意圖。
然而,如果我們因此認為這是一個僅呈現多元史觀,缺乏主體視角的劇碼卻又不然。本劇在最後第二場戲「林爽文觀點——是實」中將林爽文率領的天地會一眾如何從大里杙開始,八月失鹿仔港、十月圍諸羅、血戰牛稠山、斗六門紅雨、雜沓松柏嶺、決戰八卦山等過程,藉由舞者動作、各種音樂變化,尤其舞台中的竹竿精彩地象徵呈現,當舞者一個一個體疲力怠地由舞台右側前方,往後方緩慢前進並轉往左側,他們一個一個拔起竹竿並讓竹竿的聲音劈拍劈拍結實地打在舞台地板,觀眾可以輕易知道他們的「叛變」「起義」已經走到窮途末路,從之前歃血結盟、揭竿而起、據守叢林、全台震動,到最後剩數百會眾在冷吱吱的寒冬據守枯山困獸猶鬥,這一場戲可以說由各種場面與背景的音聲與動作帶起了巨大的感染力,除了讓我們發現整齣劇主要舞台佈景——「竹子」具有的「叢林」、「戰鬥」等多重象徵,更讓我們感受到參與林爽文事件的天地會眾最後戰敗倒下的無奈淒涼。最後一場「江湖在哪裡」以維基百科多種對「江湖」的定義詮釋江湖,其中一條為「江湖也包括社會下層階級一群不服王法、脫離統治、流離失所、不士、不農、不工、不商的非主流社會、遭受打壓的草根社群」的說法,搭配前面一樣都是被伏綁的莊大田、金娘等的供詞,可以說這相當程度已經代表著本齣劇詮釋林爽文事件的主要視角。
同時,最後一場「江湖在哪裡?」繼續前導作《誰是林爽文》的討論,同樣以舞者說講與動作變化的方式被包含在現代年輕人的聊談之中帶出,使古今有著遙想呼應的對話。卻又帶出一個新的歷史假設「如果林爽文成功了呢?」這個討論雖然開展有限,但卻顯示新一代年輕人勇於反思歷史的視野。尤其透過對於「江湖」涵義的討論,除了帶出上面所說的下層草根社群,也延伸出「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的意思,將一樁歷史事件擴大出具普遍性的涵指,是一個極好的結尾。
本劇精彩之處尚在,它還使用了多重媒材與不同音樂形式來說故事,使得整齣劇不僅故事舞得精彩,更打造出層次豐富多變令人驚豔連連的舞台效果。比如當乾隆皇帝在大朝中批評朝臣無能抵擋林爽文事變,觀眾一方面透過陌生怪異的清代官話、以北管混合電子音樂嗩吶鑼鼓點子的吹奏敲打,感受到乾隆的氣急敗壞;隨後又透過電腦影像上放大的滑鼠箭頭在台灣島圖上不同地域不斷移動,到處被點火,觀眾彷彿看見當時天地會眾迅速攻佔全台的緊張情勢;而滑鼠箭頭在台灣島各地移動的同時,影像裡面尚有已經事先錄影好的舞者以其集體舞蹈動作代表的天地會眾行進的場面。另外,比如第五場「尪姨金娘觀點——Be Water」中因為金娘在事件中扮演的宗教角色,大量加入包括單人吟唱與廟會感宗教性濃厚的音樂,之後又加入李小龍談水及各種水的造型意象,呈現了此一極不同於一般官方、男性與政治的角度,也令人印象深刻。除了多重媒材,整齣戲在不同場景不同人物表現上,應景地帶入有如傳統宮廟鑼鼓嗩吶或什麼神秘的拔高或低抑的背景樂,把觀眾帶入了歷史時間的深處,可以說正是這齣戲成功的一大亮點。
在雞屎藤舞蹈劇團這齣《大事件─臺灣刁民林爽文》的優異演出中,我看見台灣民間文化的活力與厚度。
《大事件:臺灣刁民林爽文》
演出|雞屎藤舞蹈劇團
時間|2021/12/18 19:30
地點|臺南文化中心原生劇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