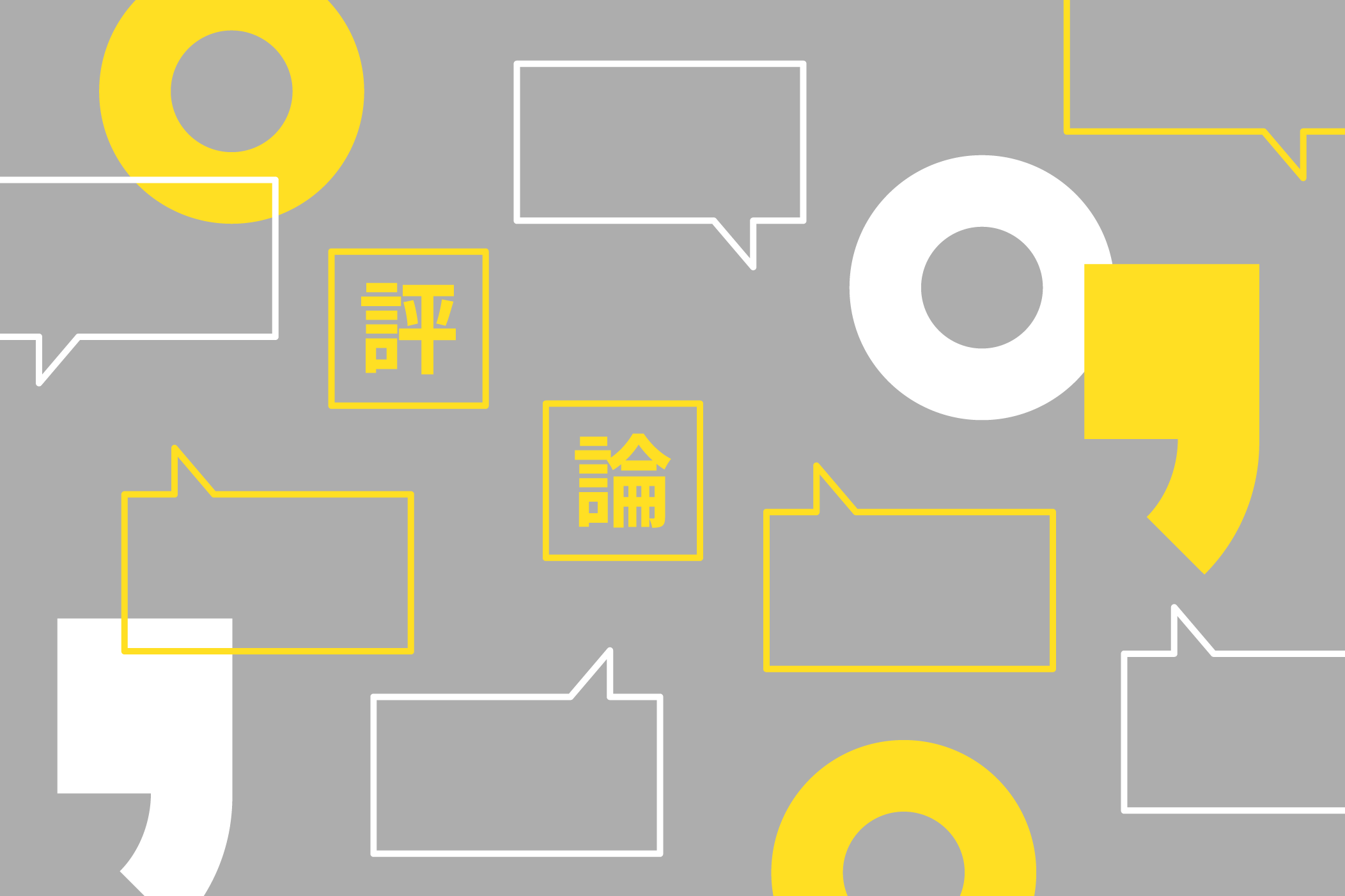
王逸如(台灣大學戲劇系)
打開電視,走進電影院,甚至只是街頭抬眼即可看到的廣告熒幕都充盈著關於人類情感的敘述。過度書寫到爛俗的情節已經將我們的情感閾值越拉越高,似乎多麼離奇荒誕的人情拉扯都不再能打動我們閱盡千帆的心靈。劇場藝術在這個充斥著奇技淫巧的敘事時代一定是相對弱勢的那個。那麼難道說客觀條件的限制就註定了劇場的觀眾可悲的只能被迫觀看「不夠刺激」的故事嗎?
我無意以上述的言論引出任何危言聳聽的結論,亦或者鼓吹劇場在今天的劣勢會帶來必然的蕭條。我願意承認,是的,劇場就是在講一些「不夠刺激」的故事!但是,這種不刺激才是最能夠矯正我們已經過分被拉高的情感閾值的不二法門!
那些過度刺激的故事情節雖然組合出了架構龐大的結構,卻忽略了一個具體人物在漫長時間中的細微情感變化。故事中的角色只是完成劇情架構的木偶,其相關的細節甚至不足以讓觀眾相信他們可以活在這個世界上,當然更不可能共情於人物的經歷了。一定程度上,情節的龐大複雜程度幾乎與人物的細節雕刻成反比,更談何鮮活?而劇場藝術的客觀條件直接限縮了情節過度複雜之可能,這反過來也逼得創作者必須在精煉的情節中展現出更多具有邏輯性的細節以建構一個角色。這樣的建構過程恰恰填補了角色鮮活性的需求,而更能扎進觀眾者空白的內心。
《如此美好》可以說是一個非常不刺激的故事。這其中有人死了,卻成為詼諧的笑料;有人受盡病痛折磨,卻還能起來說說笑笑;有人生活一團糟,卻也被遠遠的隔離在水箱之中一言不發。這個故事中,只有一個老人絮絮叨叨的陳述著他與妻子、早餐店老闆、醫生、咖啡店老闆無聊而瑣碎的日常。而這些日常都圍繞著另一個人而產生——兒子,那個在妻子離世後唯一還有羈絆的兒子。
父子親情是個過分古老的議題,我們看過父子反目的,看過多年後重逢的,看過上陣父子兵,當然也有相看兩生厭,但是我們確實很少看到只有父親一方的自白。這個自白的男人不會有別的更重要的身份,而只是一個父親,並且是一個已經孤獨到自己一個人敘述的父親。不僅如此,《如此美好》中的父親更是一個坦誠的、體貼的父親,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已經老了,與兒子產生了不可彌合的代溝,但是他沒有成為那種「討厭的老人」。他會說「你直接回台北嗎?」來替代說不出口的「你今天不回家?」;他會用「兒子會遲到意味著他跟老爸在一起很放鬆。」來安慰自己;他不想變成囉唆的父親而將所有掩藏不住的擔心與叮囑咽進肚子裡。這樣試圖理解兒子的父親在現實中恐怕是很多年輕人求之不得的。但是當這個父親站在你眼前呈現出極度期盼的表情和身體語言,而口中卻如此逞強的時候,你還忍心期盼自己有這樣的父親嗎?
戲劇舞台就是有這樣的魔力,讓觀眾瞬間帶入正在說話的父親視角。透過這雙年邁的眼睛,我們會看到,一遍遍的重複在兒子童年發生的故事是因為他的記憶已經變差了,只有這不多的還記得了;會看到他數著小時等日落是不想讓自己意識到太無聊,因為他是地表最強老爸不會囉唆啰嗦的騷擾兒子;更會看到他直白的講出「陪他到最後的是他的另一半又不是我。」的時候才發現老婆已經走了,那誰來陪老爸到最後呢?
重新思考為什麼我們很少看到來自父親的視角?作為創作對象的父親遠比與之相對的母親更加難以直白的表露。我們很輕易便可以脫口而出母愛的偉大,這種輕易乃是經年累月的表達習慣,然而父愛卻因常被冠以深沉的名號而錯失了表達的窗口。而創作者群體本身也以中青代居多,還沒到能夠體諒父親的年紀。父親們自身往往又是逞能的,不願意博同情一般把這些婆婆媽媽的瑣碎心情付諸筆尖,不可能主動為自己講話。這些疊加的條件使得劇情之視角必然是缺失的,進而讓觀眾只能看到吵架面紅耳赤的父子在設計出的戲劇性橋段中詭異地和好而無法看到來自父親那每一次深夜中孤獨的思考,而這種視角的缺失也導致了細節建構的不可能。
《如此美好》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年輕劇作家以令人難以置信的視角重現了一個父親鮮活的情感樣態,讓我們成為那個父親而感知這段父子羈絆。這種細節、這種視角才真正讓父子親情不是在唱一場獨角戲,將父與子真正的聯繫起來,如此,觀眾也才能與著父子同呼吸共命運。
《如此美好》
演出|動見体
時間|2022/3/5 19:30
地點|水源劇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