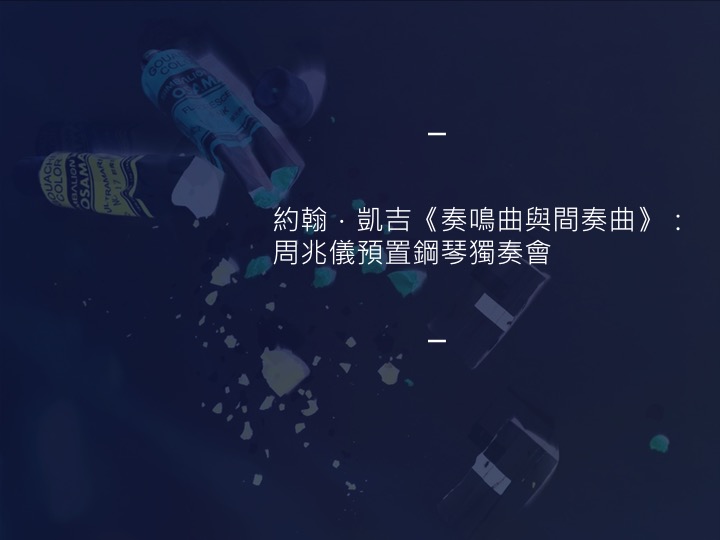
顏采騰
除了探討寂靜及隨機聲響的《4’33’’》之外,約翰・凱吉(John Cage)最為人知的,應該是所謂的「預置鋼琴」(prepared piano)了。將螺絲、橡皮、紙片等物品放入鋼琴,營造或如打擊樂器、或充滿奇異泛音的聲響效果,在現代音樂較少被演出的臺灣,仍具一定的魅力。
鋼琴家周兆儀這次演奏的《為預置鋼琴的奏鳴曲與間奏曲》(Sonatas and Interludes for Prepared Piano),即是凱吉早期廣泛嘗試預置鋼琴的集大成之作。全曲共十六首奏鳴曲,中間穿插四首間奏曲,為上下對稱的特殊結構。周兆儀則從中拆半,分成上下半場來演奏。
「西方—東方」的二元閱讀
作爲凱吉早期的代表作品,《奏鳴曲與間奏曲》當然不止於惡搞鋼琴,其中還有許多耐人尋味的創作意涵及謎團。一九四O年代,凱吉大量閱讀印度哲學家Ananda K. Coomaraswamy的美學文獻,並且接觸了印度音樂文化。依其自述,他寫作《奏鳴曲與間奏曲》的目的即是「探討印度傳統裡的『九種永恆情感』(nine permanent emotions)」,並「表達東西方共有的理念(idea)」。譬如他以鐘聲音色象徵西方、以鼓聲聲響代表東方,形成東西方的跨文化對話。【1】不過,所謂的「永恆情感」究竟是如何和二十個短曲相對應?實際上有哪些段落取材自亞洲音樂?關於這些問題,作曲家並未給出明確答案,留待後世學者不斷解謎,也留給演奏家自由詮釋的空間。
從周兆儀的演奏詮釋來看,她對樂曲的看法是十分明確的。初步來說,《奏鳴曲與間奏曲》存在著兩極相異的元素,一種是以調式音階組成旋律的、較為傳統的樂章,另一種則是讓人難聽出旋律的、仿若擊樂重奏的樂章。周兆儀的詮釋恰好符合並強化了這種「西方—東方」的二元對比式閱讀。
以〈第十二首奏鳴曲〉(Sonata XII)、〈第十六首奏鳴曲〉(Sonata XVI)為例,凱吉在曲子裡刻意保留了鋼琴音高的可辨識性,讓旋律線清晰可聞,周兆儀則予以古典風格般的雅緻觸鍵,彷彿以看待傳統調性樂曲的方式來彈奏;高音旋律線的上下起伏、以及低音重音的錯落,屬於共曉時期(common practice period)的那種堆疊情緒呼之欲出,坐在我前方的觀眾也忍不住鼓掌,大概可以看作「傳統感」(西方)的最佳印證。
與之相對的,是如〈第五首奏鳴曲〉(Sonata V)、〈第十一首奏鳴曲〉(Sonata XI)等富具打擊感的曲目,在此可以聽到鋼琴家使用完全迥異的句法,營造異樣的音樂情境,時而強調敲擊屬於鼓聲的琴鍵,是她強調的「非傳統」(或是說,東方)之處。
此外,我也認為周兆儀對「永恆情感」的對應,抱持相對嚴格的看法——依照學者J. Pritchett的見解,以印度教美學的界定,每首奏鳴曲/間奏曲應當都各自對應某個特定的「永恆情感」。【2】在周兆儀的演奏中,也可以聽到每首短曲差異極大的性格表現。在我的聆聽印象裡,情感濃烈處尤其集中於第五首至第十二首之間;前四首及後四首則相對平淡寧靜,似乎符合作曲家的核心思想——寧靜(tranquility)是所有情感的最終共同傾向。【3】換句話說,在演奏詮釋的層面,周兆儀十分忠於作曲家的美學理念。
正襟危坐:嚴肅演奏的得與失
不過,若稍稍脫離演奏的細節,還有一件事值得細思:周兆儀那「嚴肅」、「重視精神性」的演奏態度。
在音樂會的一開始,我原以為周兆儀會稍微解釋預置鋼琴的原理、或凱吉的創作背景等等,沒想到她一坐上鋼琴椅便開始演奏。雖然鋼琴家在演後表示是「自己不想分心」,但她那樣認真、投入、嚴肅的姿態,以及全場屏氣凝神的觀眾,竟讓我想起以前聽過的貝多芬《迪亞貝利變奏曲》(Diabelli-Variationen)或梅湘《對聖嬰耶穌的二十凝視》(Vingt regards sur l'enfant-Jésus)現場演出——共通點在於,演奏家都將長篇作品視為媒介,以通達某種超越性或宗教性的藝術體驗。【4】因此,在演奏前不以言說介入干擾,保留作品的無限意義及崇高價值,似乎成了鋼琴家之間不言而喻的默契。
這讓我不禁好奇:像今天這樣正襟危坐地彈/聽著《奏鳴曲與間奏曲》,真的符合凱吉的初衷嗎?
我一直認為,凱吉在音樂史上具有「傳統 vs. 反傳統」的雙重形象。前者是周兆儀重視並予以闡發的:首先,她在節目單直指《奏鳴曲與間奏曲》與序列主義的種種關聯,並稍稍提及了該曲層層循環的複雜結構,用嚴肅的方式閱讀該曲。此外,她也十分尊重譜上的預置指示(這關乎螺絲對於琴弦泛音的影響、踏瓣與預置材料的連動等等),彷彿將預置鋼琴看作精密複雜的儀器。這些是《奏鳴曲與間奏曲》非常體系化、非常「傳統」的一面。
但,從音樂史的視角來看,我們會發現凱吉還有屬於「反動」的另一面。回想他的許多創作特色,如打破創作者主觀介入及音樂線性秩序的機遇手法(aleatoricism)、對於寂靜及日常聲響的探討、甚至是拒絕標準化的手寫樂譜等等,皆是他對於既存音樂體系的挑戰。如果我們觀賞凱吉1960年的《水上漫步》(Water Walk)【5】,也能發現他竟怡然自得地在電視臺表演前衛音樂,毫不介意現場觀眾的肆意笑聲——某種意義上,這正是凱吉對於「(古典)音樂會」這種陳腐活動的回應,以及對於今日我們這種「正襟危坐」的最大調侃。會不會,如果我們太過嚴格地貫徹凱吉的理念,反而是一種最大的背叛?
老化與復生:現時意義的探尋
寫了以上這些,我其實並無批判或挑戰鋼琴家的意思。真正的議題在於:凱吉以及預置鋼琴這樣原本突兀且怪異的存在,正在歷史洪流中老去,逐漸喪失原有的張力與驚奇。原先的體制反叛者,最後被體制收編,成為能夠被「認真嚴肅地演奏/聆聽/研究」的經典文獻之一,這也是所有藝術作品的宿命。
要在今日找回凱吉當初帶來的驚奇,想必是不可能的了。如周兆儀這樣探究傳統脈絡、再現凱吉較嚴肅的形象,有其價值。與此同時,我也期待著凱吉另一形象的「再」揭露,以今日的視角重新探尋凱吉的未知之處——在我們熟知的預置鋼琴「知面」中,尋找還未被符號系統收編的「刺點」,找到還沒被書寫的未來意義。唯有如此,凱吉才能一次次地在現時(actuality)中復生,有機地存續下去。
註釋:
1、Richard Kostelanetz: Conversing with Cage (Routledge, 2003), p. 62.
2、James Pritchett: The Music of John Ca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30.
3、凱吉的原句為:「關於藝術作品所必需的情感概念,有四種白色的、四種黑色的,以及所謂的「寧靜」——無色、位於中心,這必須被表達出來。」見註一,頁16。值得注意的是,凱吉也說這種永恆情感的區分「沒辦法符合進我的作品裡。它以自己的方式存在於每個人身上,我不介入其中。」意思是情感與樂曲的對應沒有客觀答案,端看鋼琴家的解讀。見註釋1,頁217。
4、這裡似乎有個問題值得深究:《奏鳴曲與間奏曲》首演的當時,觀眾與樂評有何回應?當時聆聽的場域氛圍是什麼?我們知道《奏》的系列初演場包含最傳統的卡內基音樂廳(Carnegie Hall),但也有資料指出,《奏》的最初首演為知名的黑山學院(Black Mountain)。這兩場造成的迴響一樣嗎?我手邊沒有相關的文字記錄或報導資料庫,也許直得進一步尋究。
《約翰.凱吉《奏鳴曲與間奏曲》:周兆儀預置鋼琴獨奏會》
演出|周兆儀
時間|2022/07/27 19:30
地點|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表演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