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施靜沂(專案評論人)
此次札兮劇坊於花蓮光復推出的「路‧Lalan母語小戲節」,由三齣看似相連又各自獨立的短劇組成。由於國內COVID-19疫情未穩,「小戲節」雖原訂於九月十日、十一日在光復車站旁邊的「緩緩書屋」戶外空間演出,也預告推出網路播映版。雖然播映方式及節目稍稍歷經更動,【1】但因為是在地的社區劇場、實驗劇場,因而此次倒沒造成觀眾什麼大的落差感受與困擾。但同時,藉由知曉這樣的過程卻也洞見了節目企劃者羅織此一結合地方/部落、藝術節與母語戲劇的節目時,面臨著演出以外之技術、人力、天氣、疫情等變因與挑戰。
整體而言,筆者觀賞的網路播映版頗完整,而透過後續一個多小時的「線上分享會」,演員、創作者也能觀眾直接對話,進而形塑出「既數位又在地化的」觀戲體驗,彌補了平常看戲時,「劇終人散」後若有疑問也只能瞎猜、沒什麼機會釐清的狀態。在公開平台上對話交流,也讓筆者等對花蓮光復太巴塱等阿美族部落有點認識又不那麼熟悉的「外人」,能更直接地建立一些連結。
一開始看到「路‧Lalan」的母語演出劇目時,率先映入筆者腦海的其實是過往在馬來西亞自助旅行時,路邊綠色路牌寫著的「Jalan」;馬來語的「路」唸為「Jalan」,重複的「berjalan-jalan」則有「散步」之意。【2】但此次阿美語「Lalan」開展出的母語戲劇之路,不走悠哉路線,而是蘊含歷史與命運的重量,試圖帶觀眾進入較為深層、嚴肅的話題──所謂的「路」,不只是讀劇《11》之年輕人飆車、人們通勤的「馬路」,更是《O sakataloma’ a lalan ni Lafi'》(Lafi'回家的路)中,五零年代國中女生每天上學、放學的漫漫長路,更是《Talacowa Kamo》(去哪裡 你們)中,日治時代阿美族男人們的工作。根據演出者Awa劉于仙與Moli Ka’ti 摩力.旮禾地的詮釋,過往被日本人帶去「造路」的老人家及其家人,對於被帶去「造路」的來龍去脈,似乎有些一知半解。因而過去的些許「造路者」,似乎是以「半迷路」的姿態,成就當今所見的蘇花公路等道路前身。但他們的「替國家造路」,卻沒被多數國人記得,也沒因為這樣的歷程而讓自己的人生通向光明的道路。因而如今,我們只能透過田野、創作、戲劇緬懷當時阿美族人造路的片段記憶,讓這近乎無聲、模糊的歷史終於有機會再度被想起。

路 ‧ Lalan母語小戲節 現場演出劇照 (札兮劇坊提供/攝影|靜好寫真工作室 林彥劭)
看完戲後經初步梳理,很快推敲出上述「母語小戲節」的理路;然而,蜿蜒曲折的思緒/道路化為戲劇演出時,最觸動人們之處則在於演員、創作者詮釋戲中故事的當下,與這些部落歷史記憶隱微的交匯、深刻的連結。尤其這次穿梭華語、阿美族語的演出中,蘊含文化實踐及創作者、演出者文化尋根的真實心境/路徑。筆者認為,這是此次族語戲劇演出給人之與華語戲劇最不同,也最珍貴的地方。
透過「迷路的靈魂」、「無限的房間」、「蜿蜒山路與大馬路的對比」思索「回家」
一開始的讀劇《11》,由Fayu林采妮、Awa劉于仙及Moli Ka’ti 摩力・旮禾地共同演出;Fayu扮演在外求學、思索「返鄉」課題的少年飆仔努該;一開始,他複述著幼年時坐著棗紅色得利卡,並因山路蜿蜒而吐得東倒西歪的回憶。長大後,他因發現家鄉的道路拓寬、變直,讓他覺得「沒有不回來」的理由。但他的語氣流露嚴重的不耐煩與疏離感。相較Awa飾演的當地居民娃娃阿代代,義正詞嚴地糾正飆車的努該,Moli飾演之抓龍蝦的士官長則在提著龍蝦從海邊回來時,以老人紆緩的口吻稱年輕孩子「迷路的靈魂」,甚至把迷路之因歸為「路越來越直」、彷彿「全知全能的神創造的迷宮」。

路 ‧ Lalan母語小戲節 讀劇《11》(施靜沂提供)
在士官長如此「點題」後,觀眾開始感受到「越來越直的路」與「迷宮」意象的反差,進而有所思考,劇的主題也慢慢昭然若揭。很快地,士官長以講故事的語調向阿代代娓娓道來一則老人在山裡、城市迷路的「傳說」,然後觀眾也才恍然大悟,啊!原來是在說一個阿美族人把另一位族人騙去外地工作的事,只是Moli用一種講述古老神話傳說的語調說這樣的故事,因而蘊含反諷的味道!
然而,即使這齣劇蘊含諷意,但觀演當下筆者則被「沙烏地阿拉伯」及後續「迷宮」、「波赫士『無限的房間』」的關鍵字吸去了注意力。分享會時詢問作者才得知,原來過往的確有不少族人前往沙烏地阿拉伯工作;如此經歷在「士官長」詮釋下,也自然地連結到「迷路」的意象。同時,因筆者讀過雅美族作家夏曼.藍波安的《安洛米恩之死》等作品,也很自然地想起書中族人在外地工作卻淪落的不快歷程。但《11》對相關內容則點到為止,反而「無限的房間」、「山裡的路,不會讓人迷路」、「平坦的大路,哪裡也去不了,因為沒有人知道該通往哪裡去」等士官長寓言般,對於路的辯證的台詞顯得餘韻繞樑、引人細細琢磨與尋思。
事實上,正在學母語的娃娃阿代代和關注族人在外地工作之命運的士官長兩個角色也延續到壓軸的《Talacowa Kamo》(去哪裡 你們);這齣讀劇至此,則差不多已帶觀眾進入阿美族人/劇作者對回家之路、迷宮的理解與辯證語境;雖然讀劇以華語為主,僅少數族語單字,但接下來Fayu擔綱演出的《O sakataloma’ a lalan ni Lafi'》(Lafi'回家的路)則是全族語的獨腳戲。Lafi'這個角色雖然性別、年代和狀態與讀劇中的努該不同,二者卻相當巧合地都是「回家之路不順遂的年輕人」。

路 ‧ Lalan母語小戲節 現場演出照片 (札兮劇坊提供/攝影|靜好寫真工作室 林彥劭)
透過名叫Lafi'(晚餐)的女孩,凸顯飢餓的記憶、女性的責任及走夜路回家的恐懼
阿美族女孩Lafi'的故事,透過Fayu林采妮傾向誇張路線的演技,可謂藉由Lafi'之名雖意為晚餐,卻常挨餓的反差,帶出阿美族女國中生放學後走夜路回家,卻面臨飢餓、恐懼的青春記憶。Lafi'一出場,觀眾很快便能從耳下三公分的清湯掛麵頭、長及膝蓋的黑色制服裙,辨識出其年代與年紀;隨著劇情發展,懷舊、歷史感也呼之欲出。
整體說來,這齣戲因Fayu的族語相當流暢,舉手投足發揮少女澎湃的心理戲,而讓觀眾在觀戲當下不太會去想故事的寓意,而是在其展演少女走夜路回家、飢餓中縈繞照顧弟弟、妹妹的責任感、對未來漫無邊際的想像中,不知不覺由此連結到筆者爸媽曾向筆者描述之在鄉間生活的少時生活記憶──同樣關於飢餓,關於返家之路的遙遠,關於在溪邊抓小動物,還有讓人期待的炸彈麵包;那樣的少時鄉村生命回憶,與當今台灣鄉村地區的面貌確實不同。同時,演員也將田調時族人敘述的某種「懷念的、遙遠的感覺」演了出來,意外成為亮點。
然而,這其實是齣弟弟溺死,姐姐為拯救弟弟Calaw也命喪黃泉的悲劇。筆者經分享會得知,關於「若交男朋友,要詢問他願不願入贅」的說法,來自Fayu家鄉瑞穗部落阿姨的生命記憶,悲劇部分則與過去曾有部落年輕人因撿拾之花生被偷而以魚藤自殺的悲劇。簡言之,透過「少女沒回到家」的結局,一方面回顧部落的生活史,也暗含「返家之路漫長、路上暗藏危機」的諭示,進一步衍伸,也與讀劇中「飆車族是路上的危險因子」有所對應。再由此連結到壓軸的、關乎工傷生命記憶的《Talacowa Kamo》(去哪裡 你們),則形成了鋪陳的效果。
在「母語的路上」與百年前的族人生命史交匯
此齣短劇一開場,便可見Moli Ka’ti 摩力.旮禾地與Awa劉于仙在一近似火車站月台的空間對話。緩緩書屋的戶外舞台,背後就是台鐵光復站月台(且不時有火車呼嘯而過),再加上Awa為了讓Moli Faki聽清楚而放大聲音、放慢語速的說話,讓筆者觀戲當下,便真的以為兩人是在火車站月台對話了!
他們的對話延續在讀劇《11》時的話題──日治時期阿美族男人造路的歷史,卻也透過仍在學族語的Awa,辨識Moli說的ato Sakatan、ato so’o、Kalinko,分別為族人前往工作的沙卡礑、蘇澳、花蓮等地,再現了當今年輕人學族語時真實且生活化的「困境」!意即,年輕人雖然想學卻學得慢,因而在聽老一輩的人說話時常是人家講了一大段,年輕人則需用很稚拙的方式逐字理解,就像在學外語那樣。在此,Awa帶出了「母語」小戲節背後的重要主旨──母語如何落實在生活中;顯然不只需要各種說與聽的機會,更需要耐心、好學及友善的環境!
最後,Moli透過一段在隧道工作、卻因意外而斷腿的劇碼,與日治時期造路的前人對話,也與年輕時因工傷而失去左腿的自己對話!根據分享會時Moli所言,他十九歲時因在鐵工廠工作而失去左腿,舞台上,則是透過揣想來演繹過往族人若在隧道工作時若面臨工傷時的情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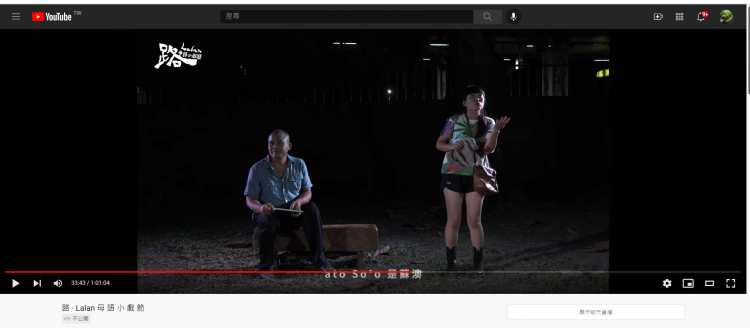
路 ‧ Lalan母語小戲節 Awa及Moli(施靜沂提供)
在當今的原住民文獻、文學中,其實不太容易找到相關文字記錄,但這樣的事卻非不曾發生。透過Moli的戲劇及行為藝術,我們不只恍若感受了那個「痛」;並透過這個觀眾和演員一同感受的「痛」,開啟想了解「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的心,也開啟另一個我們理解原住民「失去語言、歷史的痛」的角度。
當約一小時的「路 ‧ Lalan母語小戲節」慢慢在「痛」中邁向尾聲,並於Awa優美的族語歌聲告一段落,我們一方面期待此戲有朝一日變成更大型的製作,讓更多人有機會看見,也期待讀劇《11》或《O sakataloma’ a lalan ni Lafi'》(Lafi'回家的路)有進一步的劇情發展與轉折。同時,改編自《Talacowa Kamo 循山》的Awa、Moli的演出應也有能量告訴我們更多太巴塱部落的故事。
綜言之,此次演出有種初試啼聲的氛圍,讓本地、外地觀眾感受一下阿美語戲劇的情境,而從華語出發,族語獨腳戲撐出中場,並以歌謠作結,編排也算流暢。在字幕輔助下,不太懂阿美語的觀眾如我沒什麼大的理解障礙,畢竟節目內容不僅與歷史對話,也在消化了歷史後,以深入淺出的方式演繹出來!
註釋
1、八月中旬時海報原為9月11日線上同步直播,九月初改為9月13日晚上七點線上播映,後來因需製作即興字幕,延至9月14日同一時間。此外,原定劇目與人員之一,由秋郁柔演出之《Wal nha qriqun qu tuqi》(被偷走的路)改為與偕志語創作的讀劇《11》。
2、馬來語的「路」唸為「Jalan」,重複的「berjalan-jalan」則有「散步」之意。解釋請見:https://zh.wiktionary.org/wiki/berjalan-jalan。
《路 ‧ Lalan母語小戲節》
演出|札兮劇坊
時間|2021/09/14 19:00
地點|花蓮 Pasela’an緩緩書屋(此篇書寫的對象為同步的線上播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