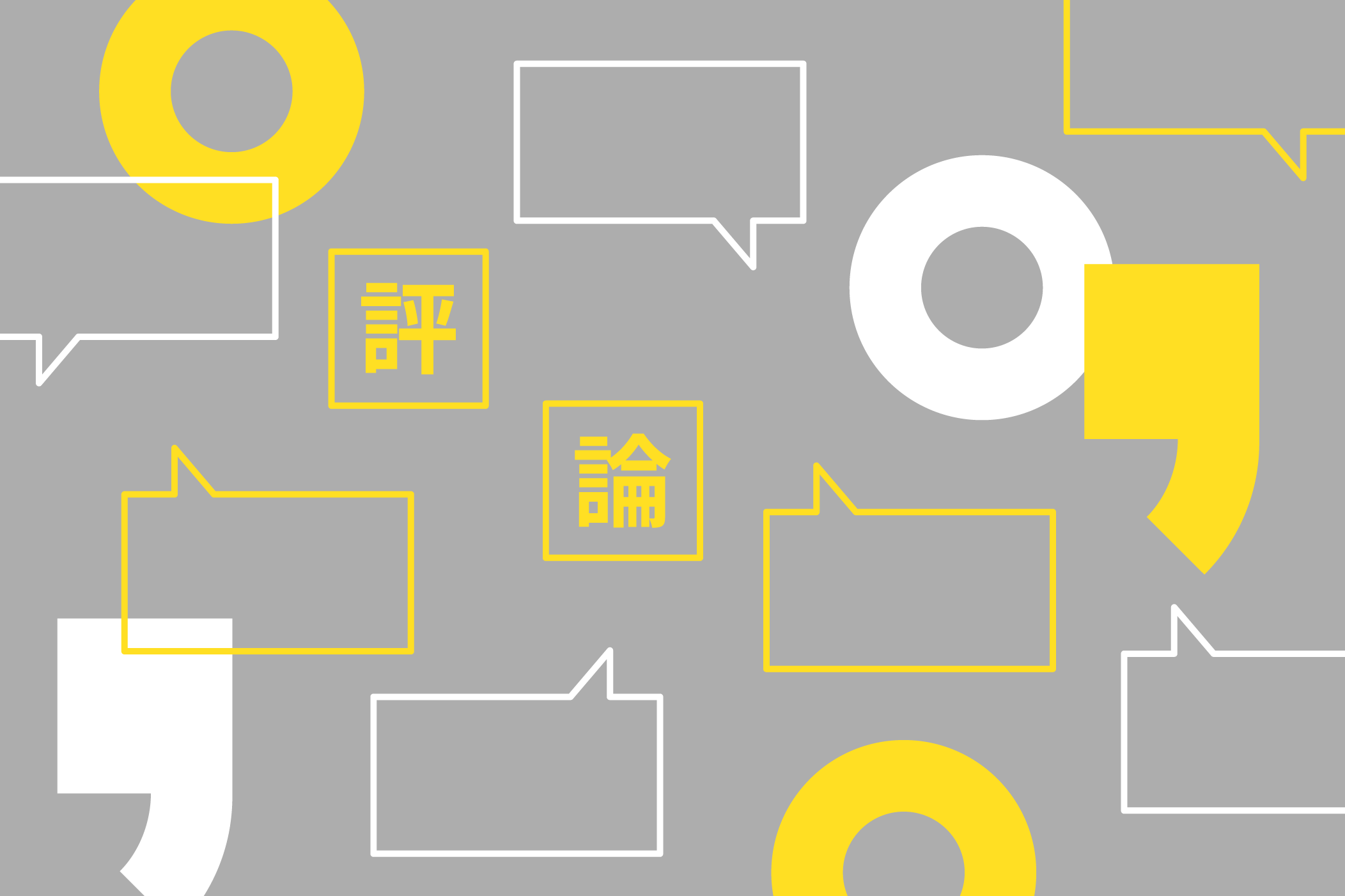
侯妍君(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舞蹈系研究所)
在疫情肆虐之下,依舊能看出臺灣人對於民俗信仰高度的倚賴與重視,即便疫情失控般遍地開花,人們依舊積極參與各項民俗性活動,亦如同在這時空下,觀眾選擇進入劇場觀賞演出,參與形式如媽祖繞境般的沉浸式演出;是觀眾心中的信仰使人無所畏懼?或是希望透過表演藝術的力量安撫動盪的世界?筆者深感,是在島嶼的喧囂與寂靜之中,找到與日常的連結以及心靈的觸動。
步入劇場印入眼簾的是滿滿的觀眾人潮,與三尊靜止而聳立在上的神祇,周圍還有幾位飾演不同角色的表演者以慢動作方式穿梭在觀眾身旁,讓觀眾猶如踏入異次元一般,陷入在魔幻的慢動作世界;《默島樂園》喧鬧的場景一如在這座島嶼中活絡穿梭在大街小巷的廟宇遶境活動,無論參與與否都或多或少存在於人們的生活中並發酵著;在《芭比的獨白》中,芭比完美的人設猶如社會對於女性的標準期待,女性與性,是恐懼還是享受,赤裸的被批判與監視著;芭比看似是對著自己說話獨自展現自身的美,但在她控制那即時影像的視角時,觀者看的與芭比期望被看的,看似皆被芭比所制約,但實際上觀眾依然有選擇的權利,牆上虛幻的即時投影畫面與控制視角同時演出的表演者,在虛與實一同呈現時,觀眾選擇聚焦的視線成了解讀與感受的最大媒介;而《擁抱日子》段落中,生離死別、悲歡離合、潮起潮落,在時代與時空交錯下,擁抱的力量過與不及,窒息的愛與思念,社會角色的扮演,醞釀成如同人生的時間線。
此次演出觀眾分為樓下的遊走區與樓上的座位區,筆者身為樓下遊走區的其一觀眾,在與周遭表演者同水平的高度觀看時,同時被樓上的觀眾、高聳的神祉俯視著,從不同觀看視角產生的漣漪亦不同反響;在第一段《默島樂園》中開始舞動的三尊神祉猶如布袋戲偶,時而如神祉般令人敬畏時而又跑出人性的一面與觀眾們互動,是神?是人?還是偶?可說是一線之隔;此時周遭的舞者與觀眾開始有更直接的互動,當他們開始推動三尊高高聳立的神祉時,下面的舞者瞬間幻化作廟會中的工作人員,大聲喝斥、指揮,強迫式的要求觀眾隨指示跟從隊伍移動,就在筆者不自覺的跟隨指示行走的同時,突然意識到有些觀眾選擇不服指令站在最外圍觀看,便停下來走到一旁看著場中跟隨的群眾,心想這樣的結果不知是盲從還是人的奴性使然,使人毫無意識的跟從,彷彿是遭社會化的象徵;表演者之於觀眾,觀眾之於表演者,甚至是觀眾與觀眾間,默默形成了十分微妙的關係,觀眾的視角成了筆者此次特別關照的亮點。他們選擇的視角某些層面也透露出人的個性,不管是高於聳立神祉的上帝視角、遊走而貼近表演者的凡人視角,或是選擇看即時影像投影或退至遠方的廣闊視角,在移動與觀看的過程中,逐漸成了演出的其一元素;透過此作品的表述可以看到在現實社會當中,人們時刻面臨選擇,在面對民主性與社會等影響,人們常常深陷於同溫層,使之無法抽離,需在客觀與主觀,理性與感性的交織下,在日常生活取得平衡。
在霓虹燈光由冷色漸變至暖色再到色彩斑駁,魔幻的音樂及吵雜人聲的鋪墊,使筆者沉浸在演出的畫面無法自拔;與生活的連結,如此接地氣又近乎人性、人情,甚至在幾次與表演者的眼神交會之中,彷彿被那樣的時空所迷惑;當黑暗中剩下一盞照亮芭比的燈,世界瞬間沉默了;最終回歸自我,在明亮的世界中與靈魂對話、與現實拉扯;不同於傳統演出形式讓視角既多變又有選擇權,即便因資訊豐富多元而顧此失彼感到小失落,但同時視角的選擇也成了觀者最大的自由。
《默島新樂園》
演出| 何曉玫MeimageDance
時間|2022/05/01 14:30
地點|臺北表演藝術中心藍盒子劇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