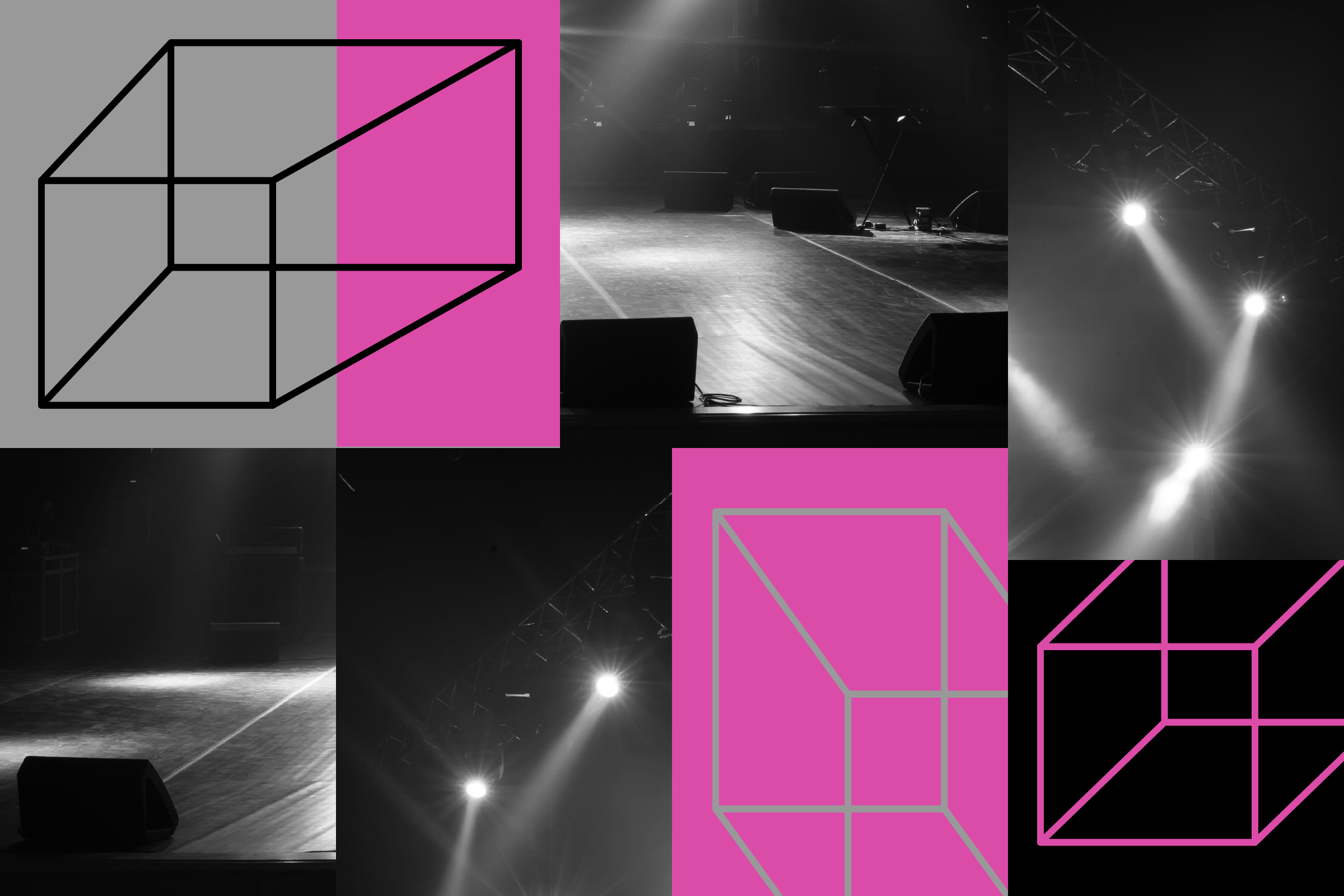
「6」與「9」、陰或陽,不僅僅是劉冠詳苦心專研的《易經》真理,亦不局限於他近年來投入元宇宙的虛擬性與回歸現實世界的劇場現場性之別,而是更攸關生死兩界、物理科學與身心性靈,還有自我神化與俗化的兩造之能。
距離上一部完整作品《我知道的太多了》已睽違六年,劉冠詳本次的長篇舞作《AI SH69VA 欲的終結版》攜手伴侶舞者朱軒萱,以及潛力迸發的青年舞者趙晨羽,一同演繹濕婆神、舞蹈之神的流變意象。本作一方面接續了今年中旬《宇宙神廟-變形記》亟欲前瞻未來性的狂妄,另一方面又拼貼了舊作片段,也是兩次令劉冠詳編舞生涯中「被賞識」的契機——高中時期的得獎作品《癢》,以及2014年紀念亡父的《英雄》。
濕婆神與編舞家的對應
在反覆自我言說的生命敘事中,《AI SH69VA 欲的終結版》比起任何前作,更像是劉冠詳梳理自身的「宇宙」,以及假「自我神廟」之名,行獻祭之實的自傳體創作。然而,台灣表演者近年來崇尚的自傳性與自省美學,來到劉冠詳這裡卻裂出了一條奇異的路徑——從「小我史」過渡到「大我史」,不是攀附於國家、民族、歷史的「過去」軌跡,反倒借鏡與台灣文化親緣性不高的古老神話來行使「自我神格化」,同時在投向「未來」的手段上,不是寄情於當代科技敘事,反而返回劇場現場性之所以仍然「在場」的藝術性臨床辯證。
印度教中的濕婆作為破壞之神、死亡之神,帶來毀滅的同時也伴隨著新生。如果要使用一種因果推論,從對 AI、Web3 等所謂「虛擬」科技對現實世界的威脅,卻同時也不得不讓人思考,究竟所謂的「威脅」是否也會帶來生態轉型的契機?原生家庭的亡故,可能也為「棄者」帶來創作能量的新生。演出中劉冠詳悲痛抱起舞者的一幕,不僅是濕婆神哀悼亡妻薩蒂(Sati)的場景,更是與抱起原生父母的經驗疊合。抑或是,在劉冠詳曾遭受過的編舞生涯低谷與挫折中,轉而投向自我流放(地理上的遷居與意義上的遠離劇場),甚至自我流變(編舞家、Youtuber 等身份跳接)。
傳說中,死去的薩蒂轉世為雪山神女,只為了讓隱避世俗的濕婆重燃對愛的希望。演出末段,濕婆與雪山神女(Parvati)的交媾之舞,結束在雪山神女用雙手摀住濕婆的雙目。按照故事的邏輯,濕婆被遮蔽了雙眼以後,額頭突然出冒現出第三隻眼,噴出能夠毀滅世間萬物的神火。同時,濕婆與雪山神女重新連結,也降生出下一代的神祇。假設將其橋段對接劉冠詳這幾年的創作生命,必然有種感傷的感慨,不過如果將濕婆的毀滅與新生映照在當代劇場的生命中,或許也有值得我們照看的另類閱讀。
如果AI科技是當代濕婆
首先,如果AI科技是當代濕婆,在近年來傳統職業為此一片哀鴻遍野的境況中,也視AI為毀滅舊有世界的那把神火。在演出舞台上不停閃現的 AI 繪圖系列,或許是普遍象徵著視覺設計師未知的未來存亡危機。同時,Web3與元宇宙也為講求物理現場性的劇場帶來了共存與否的難題。暫且不論這種程度的「毀滅」是否帶來「新生」,但不能忘記的是:濕婆的形象和變相,總是在流變與轉化。
此外,當卸下濕婆裝束、回歸肉身之我的劉冠詳,在歌曲《The End of the World》之中走向AI製圖出的創世紀與末日史,在時間性的跨度上,已不是濕婆毀滅世界而造成的世界終結,更是創作者劉冠詳上一代血脈的絕斷而帶來人生中的幾度親緣終結。這一具在台上外露的每一吋肌膚、皮肉,儼然是其父與其母留存於這世上的最後造物。
當劉冠詳在台上演示餵給AI繪圖軟體的各項「mother with…」關鍵字,卻永遠拼湊不出爾後出現的那一段,記錄母親生前的身影影像。AI 當然無法寫出劉冠詳曾寫的那首歌,也運算不出本作在澎湖首演後的那段天空閃電異象。甚至當劉冠詳以低靡的口吻道出在母親亡後,跟任何女性交媾都會一直浮現其母的病榻形象——AI 資料庫當然也無法理解為何在女像堆疊的最後會形成母親圖像的最終結果。雖然演出前後都出現把玩VR合成器的橋段,容易被理解為劉冠詳近年投入元宇宙的徵兆,但承前所述,或許「虛」與「實」在創作者的生命中從來都不是二分的事。縱使AI永遠無法逼近人性最幽微的深處,然而AI 可以學習並仿擬人性;意即,AI不是為了努力逼近AI一直做不到的,而是為了努力深化 AI 一直都能做得到的。當我們一直以為劉冠詳這幾年來彷彿準備絕棄現實世界之時,卻透過一系列人生的演算來推理出現實的不可測與不可知。
不過,這並非是為了要重新驗證劇場現場崇高性,而是在區辯出AI和人各自被賦予的使命畢竟不同,也保留了「虛/實」如「6/9」般相互提攜的兩造之能,一如濕婆的新生與毀滅——不是先後與孰輕孰重的問題,而是如何在必要時持續流轉,缺一不可地投向「未來」。
事事相生亦相剋——回到前述提及關於創作者的自省美學上而言,所有長成史、進化史的結果在大多時候都並非依循人生真實的抉擇。反之亦然,大部分的人生現況,也不一定承載大歷史敘事的肇因,而只需要在觸碰最撞擊生命的片刻,即能改變人生的下一步——這就如同在餵養 AI 資料庫時,只要一個突如其來的參數,生命的生成結果就會立即遭到重整。抑或許,真正的「69」、「陰陽」或 AI 人工智慧,真正教會我們的,是永遠記得大數據資料庫之所以為大,就是為了永恆地保留下我們能夠從中位移自我存在位置的彈性空間,並使我們得以持續向著外部世界投放下未知、未定性的訊息。
《AI SH69VA 欲的終結版》
演出|劉冠詳舞蹈與音樂工作室
時間|2022/11/26 14:30
地點|台泥大樓士敏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