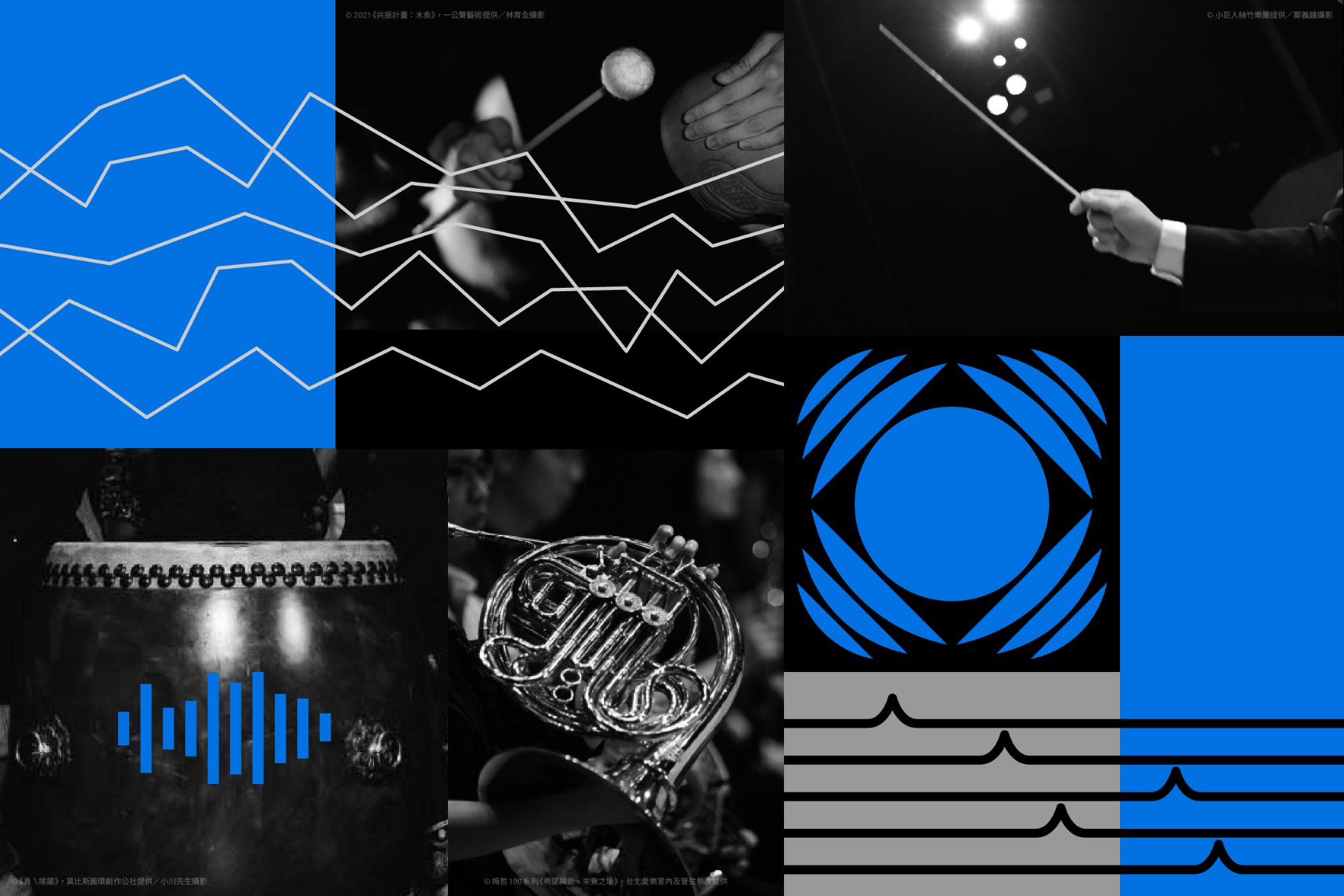
文 徐韻豐(專案評論人)
歌劇是表演藝術中最繁瑣的一門,二十一世紀的劇院經理人都在設法為這門藝術「瘦身」,尋找一種方便攜帶的方式,讓歌劇可以降低演出成本,並且反覆被演出,但瘦身後的作品卻極少有效果不打折扣的案例,而如布列頓(Benjamin Britten)《碧廬冤孽》等以室內樂為基底的歌劇,原來由百人分擔的演出效果,則全部集中回台上與樂池中的少數人。陳士惠的《給女兒的話》運用了五位樂手(加預錄音效),樂手也需分擔台詞,並僅用一位歌者詮釋所有角色,在沒有指揮的情形下演出無調性音樂,並且所有全部元素能順利拼接在一起,已是相當不容易。創作者【1】將自己所遭遇的場景與心境化為歌詞取代了現成的劇本,讓劇中人以第一人稱的方式替創作者說話。
如同本劇的英文標題《Or/And》,演出從第一景作曲家即自問出「或」與「和」的難題,隨著劇情推演,也道出我們時常用「或」來區分身份,但選擇這樣認同的人,其實同時也兼具著其他的身份或是立場,但「和」反而能將各種身份連結,這或許才是人生的普遍現象。劇情以排灣族的祭典、休士頓的示威遊行來說明作曲家的發現、用與女兒的對話來凸顯自己在說明時的矛盾。創作者使歌者一人呈現母女二角,搭配預錄的音效成為一個歌者與自己的重唱,說著親子相互不了解的矛盾,對筆者而言是全本作品中最感人的片段,用不同的英文字交替、反覆出現,也將語言的力量有所呈現。筆者以觀眾角度而言,創作者用直白的方式表達,並舉自身經驗,放入與女兒的對話,應是不難理解其想要表達的價值,然而就呈現上,作曲家所呈現的是自身參加五年祭典儀式與街頭抗議遊行的感受/哲思,轉化成給女兒(觀眾)的話,以歌者的獨白來呈現。在這樣的敘述方式下,筆者可以明白創作者想要表達的為何,也可以試圖理解作曲家的思考脈絡,但筆者在台下也有多數時刻,其實如同劇中那位不領情的女兒,難與劇中作曲家同步共情,劇情裡所呈現的母女對話,女兒因生長背景的不同,無法體會母親因離鄉背井、不同人生經歷而產生的感嘆,對於母親滿腹的想法,「只用幾句話就使母親住口」【2】,女兒在劇中對母親直言「我不是你」。
然而觀眾也不是創作者,當筆者撰寫本篇評論,回憶這部作品時,對於作曲家的女兒反而產生了相當程度的投射,筆者能理解創作者想表達的立場,但難有一模一樣的感受,正如我們生活中常見的撞牆對話,作為非當事人,我們可以嘗試理解發言者的態度,但能否完全感同身受,或是與對方抱有一樣的熱情,完全是基於彼此的人生經驗,甚或說的更玄乎一點:我們又是否投緣?
對於一部歌劇(音樂劇場或許更為精確),《給女兒的話》是以極度寫實的方式,以第一人稱呈現創作者的自畫像,舞台上有非常清晰的畫面,來呈現與創作者所經歷的相同場景(現場也說明多媒體投影的祭典與示威遊行畫面,皆為創作者的親自拍攝)。筆者甚少在劇場作品中看到創作者完全的第一人稱視角,如果創作者最想對觀眾呈現的核心價值,就是劇中作曲家的獨白,與寫給女兒的信中內容──分化與聯合(Or/And),並義無反顧地選擇聯合。那筆者其實與劇中女兒一樣,可以嘗試理解,或許也部分認同,並不能夠完全感同身受,同樣的議題可能以一部經典名著、甚或是一齣連續劇呈現更有效果。但創作者在劇中末段一句台詞「我是一位作曲家」,讓作為「一位觀眾」的筆者更多思考的,是關於每一部作品、每一個創作者都應思考的核心:一個人對另一個人想說的話,該如何說?每種效果又會如何呢?
這部作品的英文的標題《Or/And》雖然與中文標題《給女兒的話》有完全不同的意思,也藉由英文標題直接破題給女兒的信中寫了些什麼,但對筆者而言,「給女兒的話」作為標題,或許更有歸屬感,並且更點出筆者作為觀眾的直觀感受。
注解
1、本文「創作者」皆指本劇作曲陳士惠,「作曲家」則指劇中的母親角色。
2、引用自劇中台詞
《給女兒的話》
演出|國立臺灣交響樂團
時間|2024/03/24 19:30
地點|誠品表演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