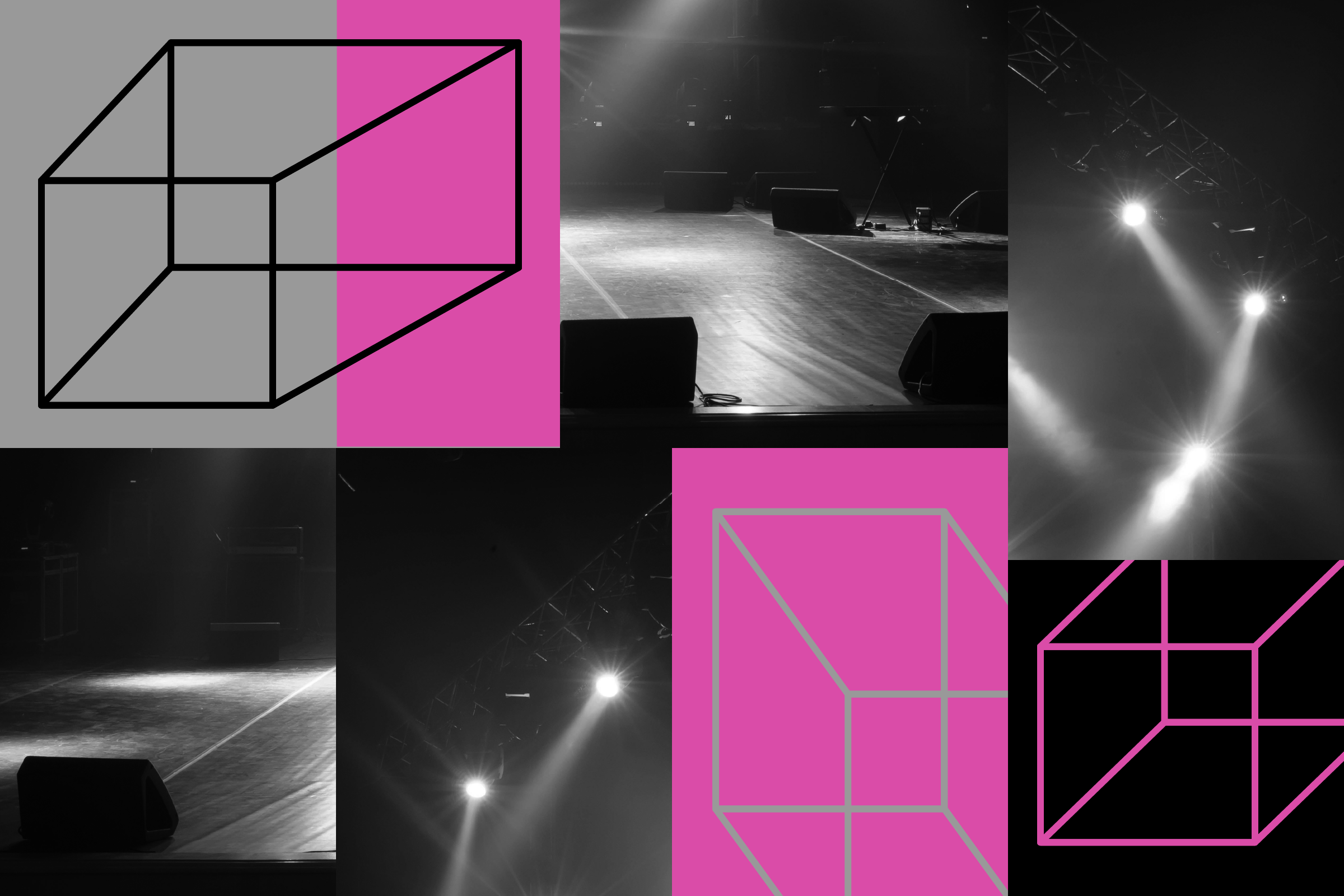
近年來,台灣的「曲盟」(亞洲作曲家聯盟,Asian Composers League, ACL)將每年要舉辦的音樂會,盡量均勻地分佈於台灣的北中南三地,並且邀請從南到北的作曲家將舊作或新作搬上舞台,定期在這片小眾又小眾的音樂市場上趕集。曲盟在2022年11月12日的「音樂台灣・作曲聯展」台中場製作,舉行在台中教育大學的寶成演藝廳。台上的演出者,很大一部分是中教大音樂系的專兼任師資,或由這些老師訓練的音樂團體。既然台灣作曲家的作品很少是台灣演奏者的必備曲目,所以演奏台灣作曲家的音樂,對演奏家而言其實也像是一個抽考的試煉。從這裡可以看出中教大音樂系和參與的職業或非職業音樂家,對自我的要求。
穿梭於「兩河流域」之間的音樂想像
因這場音樂會有兩首以台中的地景為發想的新作品,我以真金買票入場一探究竟。它們分別是林進祐的《情牽大墩》和謝宗仁的《柳綠》。《情牽大墩》是一首合唱曲;其中所謂的「大墩」指的不是台中市路人皆知的「大墩路」,而是「大墩路」的由來——當地一塊被稱為「大墩」的丘陵地。墩者土丘也,我到音樂會現場才能顧名思義。由於《情牽大墩》是這場音樂會合唱曲目中難度最高的,所以這次的演出尚不能讓聽眾完整認識該曲全貌,在此先按下不談。期待「動土」之後,未來還要再來的「揭墩」典禮。
而《柳綠》,則是一首樂器配搭很少見的樂曲,以「為豎琴與弦樂團」寫成。這首曲目先在聲響音色的想像奇度上抓住聽者的好奇心,又在「如何找到一位好豎琴手」的難度上讓人懾服。趁著演出前換場的空擋,作曲家謝宗仁上台跟觀眾解釋,「柳綠」指的是穿過台中市區的柳川和綠川;他想描繪他居住、穿梭在這「兩河流域」之間的「感覺」——更準確地來說,作曲家用音樂表達的不是柳川和綠川本身,而是對他這個台中在地人,兩條河在經過整治之後,對他的生活所帶來的「感覺」。
我不是台中在地人,但也住在台中過一陣子。我沒有住過柳川或綠川附近,但是我住過柳川西邊、另一條麻園頭溪附近(當然是整治之後)。我雖然不知道整治之前的樣子,但是到台中時,我也曾有過一個印象:台中市內的溪水,怎麼都是在水泥地中劃出的中小型渠道間游走?當然,日後我親眼見證,這些平常只是小溝流水的溪,到了風雨天也是會變成滔天巨浪,甚至能在我面前直接把小陸橋沖斷,什麼水泥都擋不住!(請到 youtube 搜尋關鍵字:「台中」、「溪水」、「暴漲」)
的確,謝宗仁所講的那種,在一座城市中走在溪與溪之間的「感覺」,至少在台北市是絕對沒有的。當台北人如我穿梭在台中時,也曾對這座城市中那份柏油路上熙熙攘攘與柏油路下溪水潺潺的強烈對比,留下深刻的印象。
以特殊演奏技巧展現波光粼粼
謝宗仁在舞台上還解釋到,他在《柳綠》中要求弦樂團使用大量的「泛音」奏法和「巴爾托克撥弦」奏法。這兩種演奏方式,都可以讓弦樂發出樂器「正確音高之外」的「額外特殊音高和聲響」。
我在這裡簡單的延伸解釋如下:泛音奏法會使一條弦的音高驟升五度、八度、或是更高,並且產生一種光暈般的空靈聲響。而「巴爾托克撥弦」,則是刻意用力向外撥弦,而讓其回彈指板後,造成弦撥本身加上弦擊木頭而產生的瞬間複合聲響。在作曲家的解釋和我自己腦補的認識基礎上,《柳綠》讓我聽到至少以下三個清楚層次的聲響:
- 弦樂團的「泛音」和「巴爾托克撥弦」密集地構成一段又一段紋理深刻卻又毛邊四溢的音毯;
- 豎琴似乎也用更突出的強勁撥奏,以及用靠近琴身上端的琴弦所撥奏出的乾燥裂聲,形成與音毯之間的呼應;
- 弦樂團與豎琴,時而規律、時而不規律地交替,演奏一個見首不見尾的旋律動機。
這三個音響層次之間的互動變化,似乎暗示了這首曲子的段落區別。這些「正確音高之外」的「額外特殊音高和聲響」,透過其錚錚的效果交織出一片淙淙的無言世界。 當我還在試圖拼湊出這一片聲響背後的貓膩時,音樂突然有了個猝不及防的變化,然後《柳綠》就嘎然而止。
體貼現代人的聲響魔法
方才謝宗仁在台上「告白」時,提到拉奏此曲的學生,曾覺得這首曲目中要求的技巧很「現代」。說實在,上述的要求的演奏技巧其實早就存在數百年以上了。只是這些技巧使用的時機,在過往可能只是短暫的裝飾性段落,在這首《柳綠》中,則密集編織為主要呈現的部分。這裡,才產生了那份陌生感。從這邊我們也可以看到,「現代」變成了不少人在聆聽或實踐音樂感到困難和陌生時,直覺性的形容詞。這段「告白」讓我在聽到演奏前,就替作曲家捏了一把冷汗。不過令人驚訝的是,在指揮許智惠棒下的中教大弦樂團學生們,在舞台上能發出上述我聽到的多層次音毯效果,表示他們將作曲家要求的技巧控制得相當不錯。
「控制」,不意味著非得執行百分之百準確,而是要達到技巧背後被期待的實際效果。我其實想到華格納《女武神》中「魔火」的管弦樂法聲響,其中弦樂複雜的音型本來就不是要求所有樂手都演奏一致的,否則火焰怎麼冉冉喚出魔力?而《柳綠》中演奏豎琴的是北市交的豎琴首席曾韋晴,難怪她一個人兩隻手的抓力,就可以和一個弦樂團並駕齊驅。當天中教大弦樂團和豎琴的表現,彷彿是整場音樂會最後劃過的一道彗星。
如果用我自己的經驗來體會,謝宗仁的《柳綠》試圖要抓住(或是喚出)的「感覺」,似乎是那份河川整治過後,使人得以漫步在光采和水聲白噪音間的悠閒和奇想。就像柳川和綠川,各少一個具體的「川」字所剩下的「柳綠」而浮現出的不具象詩意。柳川和綠川,彷彿也被音樂的詩意給整治了。不過,除了詩意之外,整首樂曲實在結束得有點突兀。音樂會後,我問謝宗仁:「這首曲子有點短,好像應該寫得更長一點?」他回道:「一首曲子聽起來覺得長,表示不好聽。聽起來覺得短,表示它是好聽的。」
現代人能為現場音樂會付出的時間實在有限,他珍惜大家的時間,也是有道理。
期待「未完成的作品」
無論作曲家自己怎麼表述,作為聽眾的我依然覺得《柳綠》的實驗性成份很高。為什麼呢?因為那些音色、聲響能帶出的直覺效果,以及延伸出的聯想力,要是在十九世紀的歐洲被試驗出來,肯定會被收錄在歌劇裡某一個場景,搭配劇本大加渲染。特殊演奏法或是調和樂團配器激發出的靈光,也許很難單獨發展成一部完整的大型器樂作品(如交響曲、交響詩),但若在十九世紀被放到歌劇中刺激聽眾的想像,不是不可能引起廣大迴響,甚至變成教科書等級的範例。或許很多人都忘記了,十八、十九世紀的歌劇中,為了讓樂團聲響盡可能吻合光怪陸離的劇情,作曲不是導入新的樂器就是將舊有樂器重新組合,以產生新的個性化音色。換句話說,歌劇其實是實驗管弦樂法的溫床。交響曲中若有新的聲響,多半是來自於歌劇中先實驗成功過的例子。
也就是說,大眾對於更新聲響的期待,其實引導著我們以為的「神聖藝術作品」,而非逆其道而行。音樂要能以正向發展的「生態圈」成長或維繫下去,不是用禁慾和高尚達成的,而是真真實實的聲響「感官刺激」(如不用高尚的詞彙如「美學創意」的話)。「創作者」的重要性就在這裡。而我私心期待,這次所聽到,其實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
《音樂台灣2022作曲聯展(台中場)》
演出|謝宗仁(作曲)、曾韋晴(豎琴)、許智惠(指揮)、國立台中教育大學音樂學系弦樂團
時間|2022/11/12 14:30
地點|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寶成演藝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