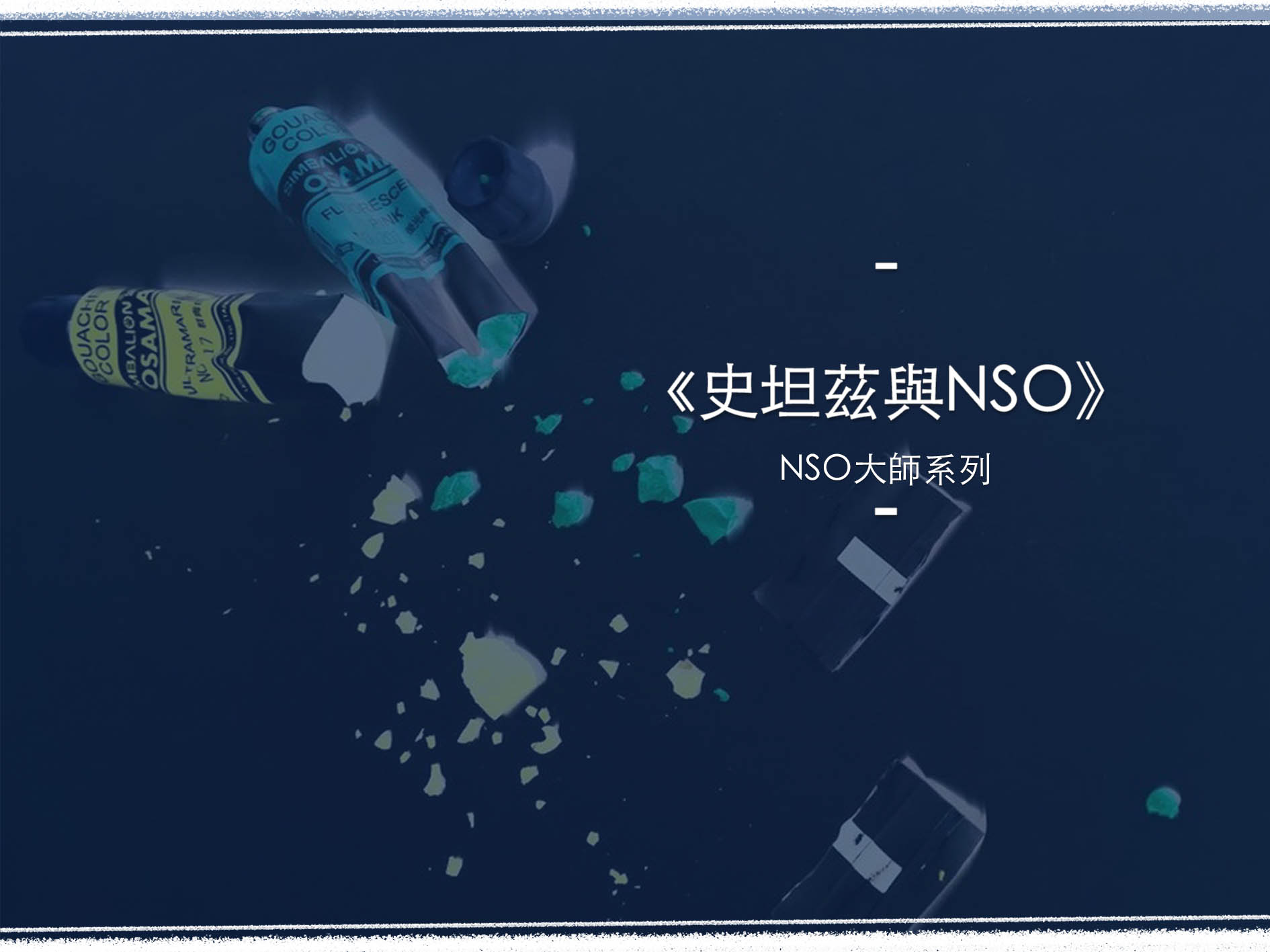
一場交響音樂會,兩首曲目,指揮家與鋼琴家各行其道,各自走上了稍稍偏離現行演奏典範的道路。雖然都是某種「反常」,其成因和結果卻都大有不同。
—
現在看來,NSO的2020/21樂季整季都是一盤和疫情豪賭而賭輸了的棋。不僅指揮、獨奏家時有更換,連節目本身都時而出現挖東牆補西牆,先前取消的節目內容幾經拼湊後捲土重來的奇異情形,這場《史坦茲與NSO》也是一例。整場曲目為普羅科菲夫的G小調第二號鋼琴協奏曲(Op. 16)、以及布魯克納的E大調第七號交響曲(WAB 107),由知名的德國指揮史坦茲(Markus Stenz)執掌全場,協奏曲則由烏克蘭鋼琴家羅馬諾夫斯基(Alexander Romanovsky)擔綱獨奏。
羅馬諾夫斯基是一位擁有先天演奏——我是指「彈奏」而非「音樂」——資質的鋼琴家,現年三十六歲的他,曾非常有機會變成一位成熟燦爛的藝術家。聆聽他十年前參加柴科夫斯基大賽時的音樂,集精緻與奔放於一身,幾乎只是被當年的冠軍特里尼諾夫(Daniil Trifonov)給掩抑了的另一潛力新秀;十年過後,從他今晚的普羅科菲夫演奏,只得聽見他的迷失與退化。
那所謂天份還是在的,只是錯失了打磨的時機而已。在第一樂章抒情而幽暗的主題,仍可稍稍聽見他晶亮的高音音色和自然順耳的語法,然而更多時候他的觸鍵流於「抽打」,雙手多以粗糙回彈的方式拍擊琴鍵,琴音猶如碎裂的晶石,也像是控制力比較遜色的霍洛維茲(Vladimir Horowitz)。這是他近年一貫而令人不解的琴音質變。在琴音之下,更多的是他對挖掘樂曲內涵的毫無興趣:到了極長的獨奏裝飾段(cadenza),他僅僅只是不斷地凸顯華彩線條、視覺效果極佳的滑奏(glissando),最終磨損了譜上特別劃出的所有主旋律。第四樂章甚至有運音法(articulation)之於同一主題的不平整,泰半時候鋼琴和樂團各執一言,想法並不契合。雖然他偶有使人驚艷的音樂表達(諸如終樂章的一些無伴奏獨奏片段,那使廳內氣氛凝結),他的觸鍵以及殘存的早年天賦對於短促艱難的第二樂章也有稍有成績,但其他地方是騙不了人的。
我不確定若今天他選擇彈奏的是較為炫技的C大調第三號鋼琴協奏曲(Op. 26),結果是否會較好;與之相比,G小調第二號鋼琴協奏曲要求獨奏家小心翼翼地平衡形式技巧上的搞怪叛逆(作為普氏的作曲特色),以及那極為強烈的情感內容表達,簡單來說就是不能用平時那種「純粹極限運動」地看待第三號的眼光去閱讀/彈奏第二號協奏曲(若聆聽王羽佳與柏林愛樂的現場錄音便可發現,連這位平時被戲稱「鋼琴辣妹」、「徒有技巧而無腦」的鋼琴家都催發樂曲中那極端而深邃的情緒了,其他人還有什麼藉口呢?)。
謝幕時獨奏家豪邁地給了三首安可曲:蕭邦的〈雨滴〉前奏曲(Op. 28, No. 15)、〈革命〉練習曲(Op. 10, No. 12),以及史克里亞賓的升D小調練習曲(Op. 8, No. 12),幾乎是太過大眾化的選曲,也有自曝其短之嫌。〈雨滴〉的樂句唱法同樣流於直覺而欠內涵,〈革命〉與史克里亞賓則無法催動鋼琴的厚實音色,甚至〈革命〉的音群聽來有怪異的顆粒及不平均感,並無法自圓其說。
其實觀眾席反應相當熱烈,不少人為鋼琴家起身歡呼。原因不難猜見,普氏的第二號鋼琴協奏曲在台灣是比較冷門的曲目,觀眾自然沒那麼挑剔;再者,羅馬諾夫斯基不只在觸鍵,也在表現特質上偏向了霍洛維茲——用炫麗的技巧堆疊音樂的外觀,掩蓋他們相對貧乏的音樂內涵,同時懂得以熱門(安可)曲目煽動觀眾心理,使人為之瘋狂。只是羅馬諾夫斯基在技巧成就上終究和霍洛維茲相差一大截,因而顯露了他的內在匱乏。
在歲數上,羅馬諾夫斯基已離中年不遠。知名學者兼樂評家薩伊德(Edward Said)就曾寫過鋼琴家步入中年可能面對的困境,他說:「四十歲之後,當叛逆小子,往往未免傻氣,要裝老年的權威,又還過早⋯⋯。一個鋼琴家如果既不再是神童或新科大賽冠軍,又還舉目不見老年的收成,其中年危機就相當可觀。」【1】三十餘年前對於當時鋼琴家們的洞見,如今竟仍能在羅馬諾夫斯基這位曾經的布梭尼大賽(Busoni International Piano Competition)冠軍的身上得到印證——他的觸鍵變化及內在的音樂思想,似乎也呈現了年少才賦不再可行,不知從往何處的悶局。這是《史坦茲與NSO》的上半場,淺碟而炫技化地之於普氏第二號鋼琴協奏曲的範式背離,也是一位曾經的鋼琴大賽得獎者在十餘年後所遭遇的一場冥頑困境。
—
下半場的布魯克納七,指揮家史坦茲近幾年方出版該曲的專輯錄音,是其招牌曲目之一。他的指揮詮釋,其實在音樂會後招來了些許不滿與批評的聲浪。理由不外乎是「演得太快了」、「不連貫」等等,似乎顯示了,他指揮棒下的布魯克納風貌與眾人對於該曲的既定印象並不相同,因而惹人反感。
這些批評其實不無道理。在近年的這群新、中生代指揮之間,確實流行著一股將布魯克納演得飛快,又抹去沈思與宗教情懷的風潮,走的是和一群廿世紀的演繹——包含約夫姆(Eugen Jochum)、汪德(Günter Wand)、以及不可忽視的傑利畢達克(Sergiu Celibidache)等人——相異的路線,而這些大師的經典演繹,也就是人們對於布魯克納交響曲既定印象的來源。而史坦茲的演奏是如何地「偏離」上述的風格?在一般被視為輓歌的慢板樂章,史坦茲竟用了明顯偏快的速度,到了B段中板(Moderato)更是飛速而忘我,好似毫不將緬懷華格納的哀悼之情放在眼裡⋯⋯。在整個下半場,史坦茲手舞足蹈(尤其是詼諧曲樂章),毫無嚴肅之風,到底又把布魯克納音樂裡的宗教肅穆之情放哪去了?就此來看,史坦茲確實也算是「偏離軌道」的一員。
但,布魯克納七這首曲子本身的「延展性」與「動態」本來就比我們想像的還大。在NSO前一次演出布魯克納七時,指揮呂紹嘉其實就給了我們新鮮而深刻的見解:他認為第七號交響曲(他特別指開頭的二十小節)傳達的是「人生真理的追尋」以及「生命的循環」等概念,而他的演繹也確實如其所述,整個第一樂章生生不息,三個主題擁有動態式的發展如流浪漂泊,思緒不斷往外飄移,雖以德式樂團的音色為標準,聽來卻不死守於傳統的宗教、管風琴音色等靜態的概念。在我看來,史坦茲也是如此。我聽聞在演前的下午專場導聆,主講者詹益昌本來在投影片中描述了各個樂章的內容與特色,但聽完彩排後他卻深感有異,並在詢問了指揮本人之後大幅地刪修其投影片文字。由此可見,指揮是刻意地要離開傳統的路的。當他做出如此宣稱時,作為聽眾的我們,或許也應放下心中幾乎成為意識形態的衡量標準。現在,有容我再次細細談論史坦茲的演繹:
雖然帶有對比極大的彈性(rubato)以及整體偏快的速度,但史坦茲的演繹並不流於隨性輕率。在我聽過的所有反常演繹裡,史坦茲其實是最有內涵,也最「德」的一個。NSO在他的領導下,音色變得極為凝鍊,連平時吹奏風格彼此大相逕庭的木管部都被訓服地服貼(特別是平時抖音極大的長笛首席,當晚竟能和弦樂音色完美地融合)。我們大可將他的詮釋比擬為錄音盤帶的扭轉——保有大多德式樂團的特質,只是被整體一致地拉伸為較為急促的樣貌。在第一樂章第三主題、以及發展部相應的段落都帶著很特殊的機械式行進,稍微可見他稍受古樂運動影響的結果,但從諸些第一主題和其變體看來,大提琴仍大開大闊,音色渾厚,仍然多是承自前一世代的遺緒。
第二樂章雖快,但其中板(moderato)並未真的超出樂譜指示,依舊落在「中板」的範疇內,充其量只是和眾人的習慣不同而已。重要的是,那是言之有物,足以激起充足情緒渲染的快,反而曾有太多其他指揮堅守慢速,卻仍乏善可陳。在音樂會前聆聽他的專輯錄音時,我其實對他的速度設計深感不以為然,但他和NSO的現場演奏中,快速之中能聽見指揮注入的強大意念,這是他徹底地說服我的地方。
詼諧曲(Scherzo)樂章則是當晚最佳的演奏。史坦茲在A段所添加的大幅音量突強突弱、速度變化空前絕後,猶如驚濤駭浪,效果極佳;若前二個樂章演得太過沈重拖沓,恐怕此樂章沒有辦法這樣演奏。視角大一點地來看,史坦茲確實會在大段落前後刻意留下較大的空間,使得音樂較不連貫。不過我倒不認為這對其詮釋有何損傷,因為他的樂思本來就是不斷向前推動發展的(這點與傑利畢達克橫向地無限開展的方式截然相反)【2】,音樂從而不凝滯於篇章極大的前兩樂章,而有加強後兩樂章表現力的作用,史坦茲的處理無疑也稍稍減緩了這首交響曲頭重腳輕的毛病。
縱使史坦茲所詮釋的布魯克納七是多麽奇異,和無盡沈思的傑利畢達克相比是多麽躁動,我們仍難以忽視他所帶有的傳統,以及自成一格的強大說服力。一樣都是「快」,古樂指揮赫爾維格(Philippe Herreweghe)和香榭麗舍管弦樂團(Orchestre des Champs-Elysées)的唱片錄音就是對於布魯克納傳統更徹底的挑戰與鬆動,論述輕盈而有透明感,相較之下史坦茲的「怪」只不過小兒科而已!我倒認為,在布魯克納的演繹上,史坦茲和呂紹嘉的光譜較為相近,都是基於德奧脈絡(注意:不是陳舊的「德奧正統」那種傳統)之上的小小變體。這是《史坦茲與NSO》的下半場,表面上創意十足,但腳底下仍深植於傳統的反常合道。
—
對於「反常」的倫理界線何在,在《史坦茲與NSO》的兩曲演奏之中有其線索。演奏詮釋雖如發明術,雖由人各顯神通,卻並非樣樣可行。羅馬諾夫斯基的缺失雖大半來自他自身琴藝的失調,另一不可忽視的是普氏作品中自己形成的規範性。倘若任何鋼琴家拒絕對樂曲內容及邏輯發表自己的見解,則必定失敗;說得簡單些,我其實並不相信任何一位純粹的「炫技」鋼琴家能真的彈好G小調第二號鋼琴協奏曲,除非其炫技是刻意地對曲子裡的強烈情感提出抗辯。羅馬諾夫斯基偏偏顧此失彼,他的缺失流於盲目(blindness)。
在史坦茲那端,我們則聽見了音樂的開放性,而那開放性也是源自於樂曲本身的。我相信史坦茲對於布魯克納的體悟和諸位老大師其實相去不遠,只是表達的語彙風格不同。與其稱他「反常」,倒不如說他其實是在做一種「除魅」的工作——將大眾誤將厚重論述、嚴肅態度作為不可侵犯原則的誤解除去。他的詮釋並非完美無缺,但我更困惑的是那些無視於他散發的強大說服力,而堅守於自身陳舊標準的聽眾。
終極來說,音樂詮釋有服人心與否的普全標準,那標準和樂曲自身脫不了關係。這全端看樂迷是否願意放下心中成見,更深刻開放地體悟樂曲與詮釋了。「反常合道」的「道」理在此。
註釋
1、薩伊德:《音樂的極境》(2009,彭淮棟譯,太陽社),頁82。
2、同樣可參考薩伊德的樂評文字(同前註,頁123)。他寫道:「柴利比達克⋯⋯將音樂視為一種橫向發展的質地,在無限的悠閒中披展,而不是在時間裡發展。」另也有樂評人形容傑氏的布魯克納演奏在時空中不斷擴大,深入異次元空間。
《史坦茲與NSO》
演出|NSO國家交響樂團、史坦茲(Markus Stenz)、羅馬諾夫斯基(Alexander Romanovsky)
時間|2021/05/08 19:30
地點|國家音樂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