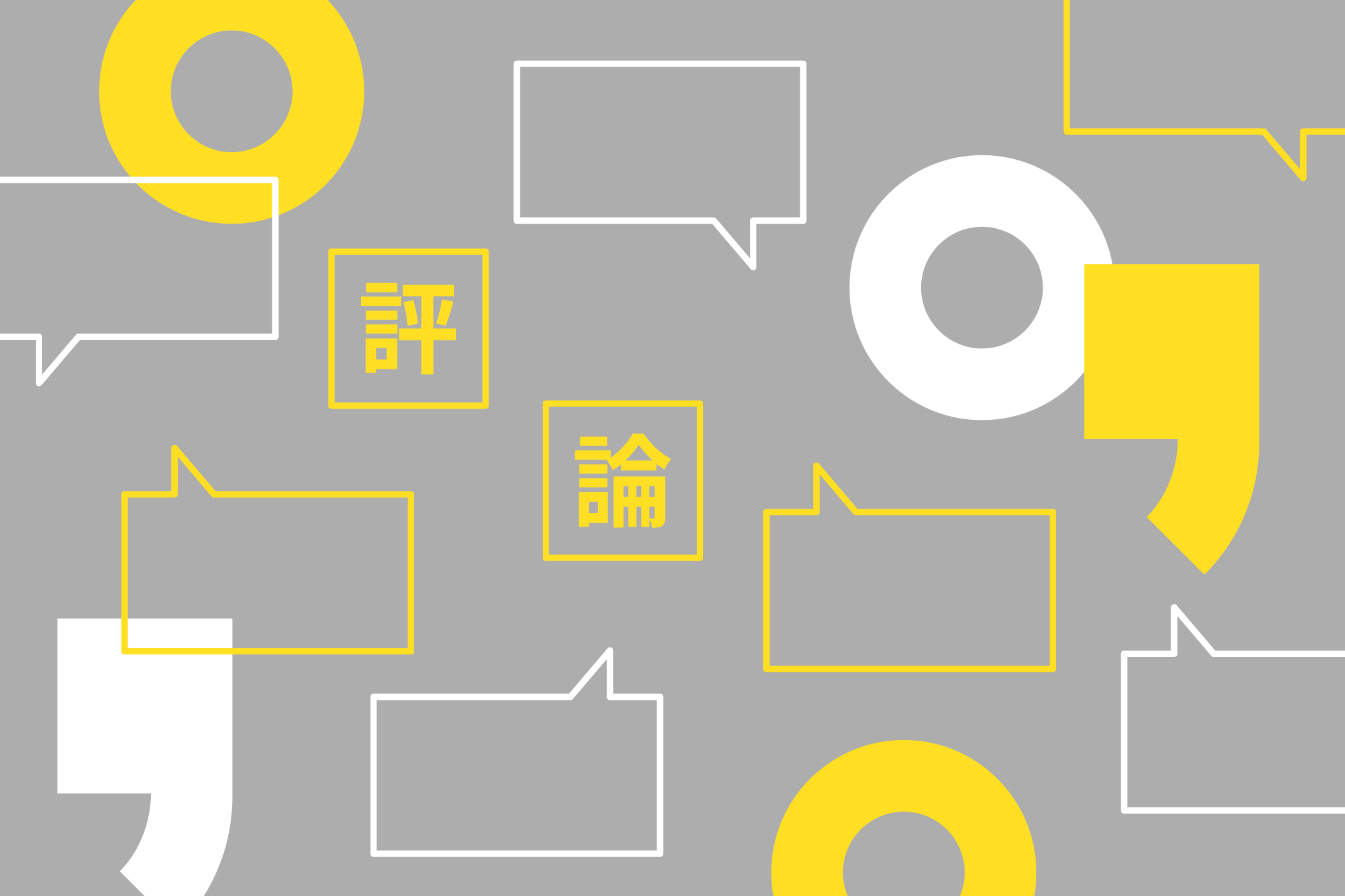
文/徐瑋瑩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博雅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人要以怎樣的姿態存在於世界?面對困境如何自處?生命能否找到救贖?這些問題是視覺藝術家暨編舞家潘大謙創作的核心問題。他一向關注全球化與資本主義秩序下人類無奈、荒謬、冷漠的生存樣態。索拉舞蹈空間之前的作品《歐西打街》(2014)、《水圍花城》(2016)、《打南無_漫遊者》(2017)、《直線迷宮》(2018)都顯現冰冷、疏離的色彩,凸顯工業化、資本主義社會中,人的渺小、孤絕、無助。舞作裡的人或有掙扎、或默然接受,但是都受困於現實,毫無抵抗、沒有出路。潘大謙過去的舞作總是帶著一片暗黑的色彩,看不見未來,也盼不到救贖。
然而,今年的作品《平流層》翻轉過去的低氣壓,可視為舞團開啟新階段的轉捩點。作品蘊含一絲力量的曙光。遊走在浩瀚穹蒼中的渺小人類,需要面對平凡孤寂的現實,然而,生存的姿態是可以自我決定的。此次作品中的自我,不再只是被監禁、被設定、無力量的遊魂,而是具有能量、不慍無懼的行者。不亢不卑,是此舞作設定的存在狀態。由於不亢不卑,觀賞過程我感受到寧靜悠遠、安心放心。生命雖然游移於世界、漂浮於穹蒼,不斷流變,卻舒緩安穩。順風逆風、順隨情勢。縱然平淡,卻也能細細品味其中的微妙,享受每刻當下。
《平流層》是氣象學名詞,又稱同溫層,位於「對流層」和「中間層」之間,沒有「對流層」的上下激烈運動,而是以水平的方向流動,相對穩定平靜。舞作構思的空間設定架構出平和穩定的舞台基調。這個基調由視覺、聲音、動作三者疊加呈現,將觀眾帶入時而從太空中鳥瞰地球的廣大視野,時而貼近人生存樣態的近身觀察。鳥瞰的視角讓我們有距離的觀看地球地景,體會人的滄海一粟。貼近生存處境的觀察,讓我們看到人與自我、人與他人之關係。抽離所處的世界,由更高的天際俯瞰,得以看清、也能看淡世間一切。索拉舞蹈空間所展望的新里程,來自看待世間萬物角度的揚升所產生的新觀點。以成果論斷日復一日的工作,或許徒勞;但是沉浸在每個經驗當下,又是另外一番體悟。
舞作由遠觀與近窺兩種視角交叉而成。開場製造出平流層遼闊平穩的空間,結尾以單人在黑暗中走向微光處收場。舞台雖仍陰暗,但是舞者走向微光,生命雖然未知,但是富有持續進行的勇氣。
開場,三大片厚磅皺褶的牛皮紙在舞台地面製造出浮動的高低雲層,配合張漢恭現場吹奏的遼闊低沉聲樂,使觀者與舞者一同進入廣闊無際的大氣層。當牛皮紙被緩緩升上天幕,紙上的皺摺與舞台光影變化,幻化出猶如從高空飛機上向下俯視的山河大地。光影色彩與牛皮紙結合的巧思,加上現場的聲/樂,刻畫每個片段的情境,開啟大氣層體驗之旅。正是此種離開地球表面的幻覺塑造,觀者的身體感進入異於被地心引力拉牽的日常重量,而有種飄然離世的感受。以此身體經驗開場,看待世間萬物的角度就有超然的可能。看似困頓、無望的生活也能是一幅畫,是時間流變中的過度。既然一切都在變化之中,生命的未知成為希望與期許的動力。
然而,舞作並不停留在遠望的欣賞之境。近觀的部分,使人不忘生活在日常中的困頓。當天幕燈滅,舞台變暗,燈光聚焦單獨舞者與他所僅有的一盞搖晃燈泡時,探尋生命出路的意象在對照下更凸顯。遠望與近窺,兩種視角的交替呈現,我認為是此舞作最精采的巧思。
潘大謙沒有使用今日表演藝術界常見,將日常生活景象「直接」置入劇場,來凸顯劇場中的疏離效果,為了使觀者能理智冷靜的思考,或是相反的,製造沉浸式的劇場事件。而是用「情」至深的藝術化舞台景象,透過對比的手法,感動觀者。即便舞台上的道具都是冰冷、工具性的器物,如欄杆、斜坡、木箱等。然而,這些器具的使用不只是人與人、空間與空間的隔離物,而是透過這些隔離中介所產生的阻礙,人與人試圖連結、超越限制。正是此能動與努力,使人有不愧於存在的尊嚴。
於是,我感受到限制的價值,徒勞的另一種意義,物質化世界背後所彰顯的情感連帶,創作摸索中的蛻變。似乎也感受到一位不太講話、看似理性、一直處理社會議題的藝術家,生命深處對世界、對人類用情至深的動力。他一直探討人類異化與物化的困局,應該是來自內在無法壓抑之情不自禁吧。
《平流層》
演出|索拉舞蹈空間
時間|2022/10/29 19:30
地點|高雄正港小劇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