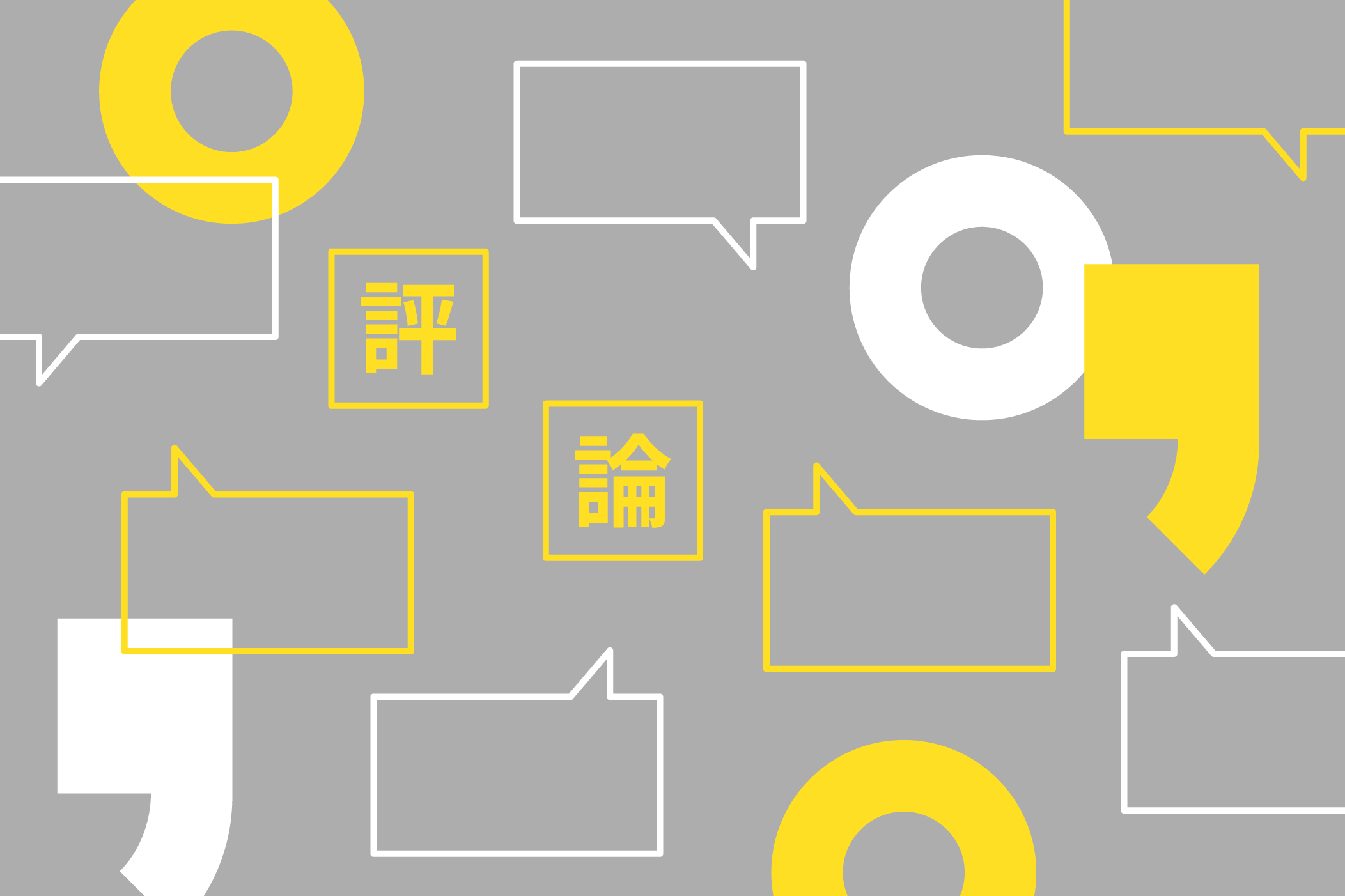
李橋河(中研院民族所 )
手路(tshiú-lōo),指的是精湛技藝和手法,是用雙手累積出來的記憶,也是這些祖傳技藝的表演者——對林正宗來說,他所要親近的目標,便是傳統藝術身體表演的「腳步」和「手路」【1】。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創作者在面對要如何學習傳統的過程當中所面臨的選擇,而他又如何將其中思考呈現在廟前埕庭之上。
馬戲式高蹺陣頭,以及雜揉兩者的身體實驗
整場演出可分為兩條來回接替上場的平行線,在木柵忠順廟前分別展現出高蹺馬戲的兩種型態:一條是馬戲風格的高蹺陣頭,將高蹺的技巧進行馬戲編排來表現廟會的熱鬧歡騰;另一條則雜揉並抽取陣頭與馬戲元素,嘗試與高蹺、牛犁歌敲子等陣頭物件發展身體的形式轉化。於此,廟埕不再只有熱熱鬧鬧做廟會的樣子,在廟埕學腳步的沈澱也開展出學習傳統與嘗試創作的時空,使高蹺陣群眾遊藝以及身體實驗創作的兩條線在整場演出中不斷交替、覆蓋。
在演出一開始,廟會的熱與鬧率先登場,表演者腳踏三尺舞弄著文武高蹺,使在繽紛的馬戲編排中提供了彷如廟會的歡慶現場。在這裡,塑膠感是其中重要元素:透過這些日常物件的拼裝重組,以塑膠呈現傳統藝術的基本樣貌;同時,閃亮的塑料感也展現出一種俗擱有力的虛像模仿。這種模仿的材質既是椅凳、也是輪胎,又是演員身上的反光彩條,亦是滿地的紅白塑膠袋。這些日常可見的材質正呈現出一種俗而有力的質感,讓我們在看到民間的神像、大仙尪仔、涼傘、令旗等傳統形象時,也為這場廟口盛宴添加仿若動畫般絢麗奪目的閃亮色彩,展現出一種透過塑料感進行仿擬與想像的親切形式。
在接替交纏的另一條情緒中,廟埕則被嚴肅地作為混雜傳統、轉化形式之所。首先,阿寬【2】伴隨唱起的牛犁歌敲響敲子,將身體屈成團狀接連抓握起落下的這雙木板,手腳因軀體瞬間收放力量來往收縮,上身則搭配下身扭動而晃動;他拾起塑膠椅夾在顎前作鼓擊打,又放下、凝視這張椅凳後翻身躍上任其撐起全身重量。繫上鈴串,他一方面用身體去製造聲響,另一方面也用動作去回應這樣的聲音,以此步步踏出民間陣頭中草根俚俗的表演方法,讓聲響與動作相互構成、互相回應。在下個段落中,有別於因踩蹺高超技術所展現出在驚險與驚嘆之間的刺激與滑稽,阿寬反而試圖擁抱踏上高蹺時所應有的那股「失控」——單腳踏蹺的他形同跛著,這時雙手撐地的蹺不再是踩在足下的支點,他由此將高蹺重新定義為探索身體可能性的物件,而不是一味延伸完整人體既有效能的工具——在痛苦、費力的過程中,高蹺的失控轉身為我們開啟關注身體轉瞬勁力的另一扇窗。這些與傳統形式和物件創造出的表達、尋找和嘗試精彩而充滿張力,深刻表現創作者對於現代形式動態性的挖掘與反思。
串場與在場:「看」鬧熱的凝視主體
在兩條主線外尚有一條穿插其中的支線,以帶有秀場氣味的主持將場與場進行串聯。在其中,主持人虧起阿寬跳得過於「傳統」的牛犁歌,要他多練練「伍佰」等更現代流行的歌曲;而在秀上歌藝時,主持者則連帶帶起了線上的「手路先生的首錄直播」,邀請觀眾各自用自己的手機再次齊聚於臉書之上。到了演出後段主線與支線逐漸交雜難辨,隨著馬戲的退場,淡藍大旗被批上廟埕隨風飄揚,阿寬身上扛著滿肩的高蹺吃力地站上舞臺,慢慢被負重壓垮而將蹺留置臺口;他用身體扛起傳統的包袱,儘管試圖將其延展、馴服,但他的無能為力也讓演出在不盡和諧的倉促下告終。此後,主持者再度慢步踏上舞臺、拿起直播鏡頭靠近,並且靜靜拍下空寂舞臺上散落成堆的蹺。至此,即使戲中串場偶有不連貫甚至獨立成章之處,但我認為這樣的結局設計可謂本作極其重要的反轉,正因為它總結了一種觀看者(不)在場的後設視角:他既是見證者也是放送者,鏡頭前空無一人,但他又是臺上之人——於此,他既分享著目睹四散高蹺的落寞,同時他也正被臺下觀眾閱讀出一陣悵然。
觀戲如此,觀看傳統藝術亦然。在廟口、在臺下,透過手機直播邀請觀眾再一次在雲端轉傳一個個關於現場的擬像,不斷挪移的椅凳則隨機座落出各自觀賞奇觀的視野。或作看戲觀者、或作廟口群眾,手機和椅子人人皆有,人人手抓板凳穿梭在廟前各處,開起鏡頭找尋最佳視線,椅子堆放高高低低,人們拿著手機前前後後。從看待廟埕演出的角度出發,這提供了一種窺看廟口的位置與方法,它兼具機動性和集結性,同時也代表了一種「看」熱鬧的凝視主體;這些片段再再揭示了以視線和身體作為廟埕觀賞者的基本構造,讓人盡情享受在場親近傳統的樂趣,同時也表現出採集踏查的藝術家在其中思考學習、模仿、創造與實踐的方式。據此,這種在搶救與發展之間無法取捨的兩難似乎始終存在,親眼看著它卻只得遙想見著它的消失,而急於分享觀看視野的背影則反而看起來更顯失落黯然。
整體來說,暖亮熱鬧的歡快馬戲與冷光聚焦的身體敘事形成強烈對比,然而這個創作雖將兩條敘事軸調度得工整,可惜最終似乎發展出的是兩條輪番上場卻無法聚合的平行線條:一條是要學習精湛技藝加以發揚的我,一條是從其外相提取靈感進而發展的我,這兩條線的自我在過程中與其說是穿插,不如說彼此競爭、相互打斷,最終在乍然的收尾下難以收束協調。但對我來說,兩條線揉合的困難與勉強正巧誠實而誠懇地表露出創作者對於田野踏查的反思——踩著高蹺的腳步前後晃蕩,終難平衡。是該踩著高蹺延伸身體,繼續精煉出「手路」的形狀;抑或是以高蹺作為支點擺弄身體,盡情發揮「手路」所能見到的視野?在戲終人散、廟埕再空之後,這或能提供其他種觀看傳統的態度,當再次拉著板凳、拿起手機,期待我們可以看見「臺味馬戲」的下一段旅程。
註釋:
1、見於演出宣傳影片〈Jérôme Thomas 講圓劇團《手路》Thunar Circus X Compagnie Jérôme Thomas《Main Agile》〉以及〈圓劇團的馬戲人生 - 手路〉。
2、林乘寬飾,此名見於2022年圓劇團《手路》電子節目冊〈手路先生的回憶錄〉,描述一名喜歡陣頭文化而與手路先生一起練習、實驗這項技藝的少年。
《手路》
演出|圓劇團、傑若・湯瑪士劇團(Compagnie Jérôme Thomas)
時間|2022/03/25 19:30
地點|木柵忠順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