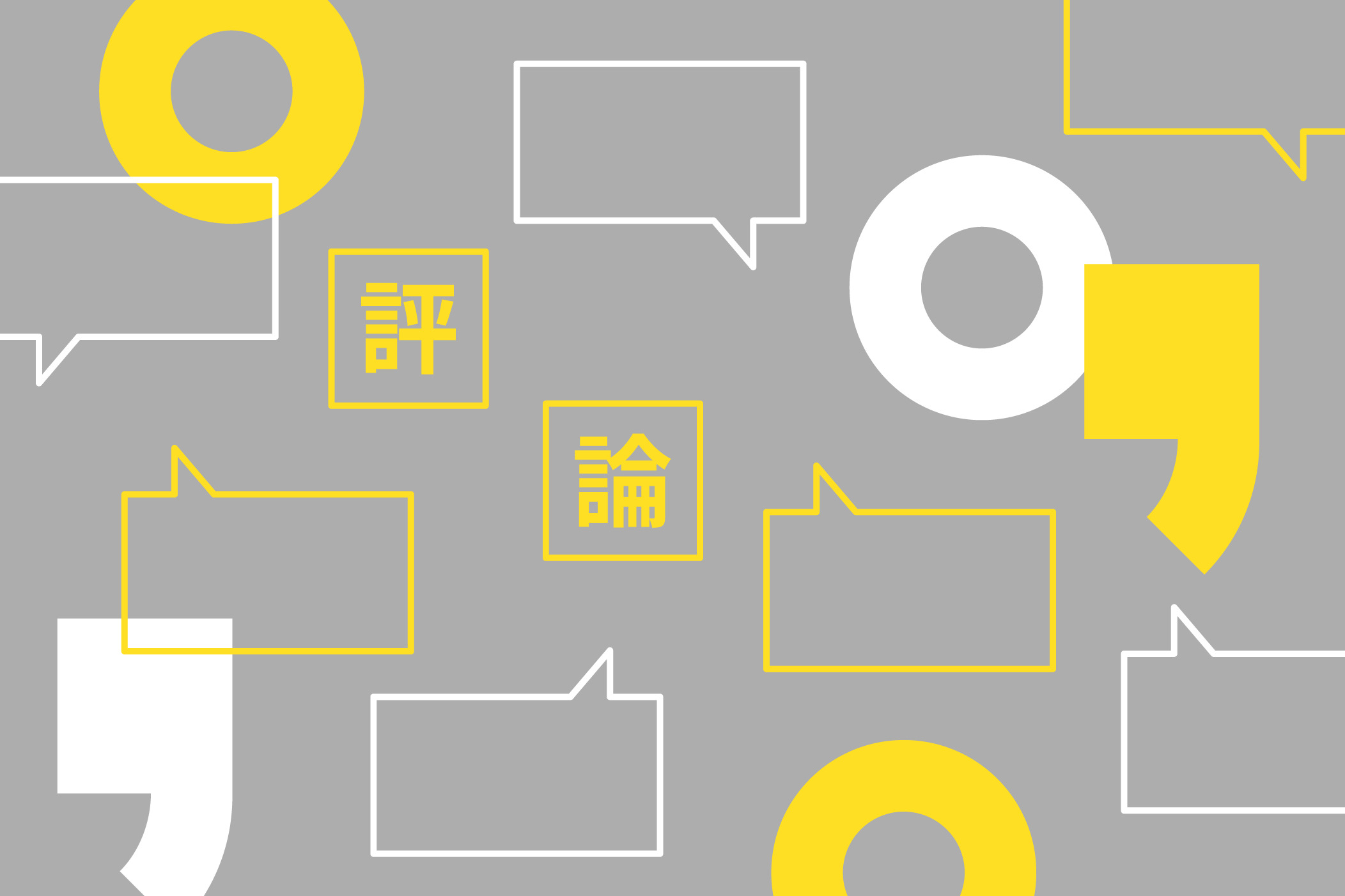
謝雲陞(國立臺灣大學戲劇學系碩士生)
張愛玲以冷酷的眼寫三十年如沉月的悲劇,京劇《金鎖記》則以戲曲特有的點線結構【1】讓曹七巧有了自述心迹的溫柔可能。劇作家揀選季澤再訪、長安裹腳為兩大高潮,在「線」的敘事延展中,以唱段為「點」的駐留,曹七巧得以發聲、得以抒情,對三爺的渴慕從「也要你留與我半點真情」的屈側,到「燈前對坐如夢杳,茶香回甘細品嚼」的綺思,最終「一顆真心盼不到,一點真情早已拋,一絲絲情意、竟也如夢杳」的幻滅,曹七巧的情感歷程在劇作家筆下更圓潤,與張愛玲「一顆心直往下墜」的酸楚、自悔、空階滴到明的悵然大有不同。
張愛玲輕描淡寫長安裹腳,當作曹七巧興致勃發、街坊鄰居的「笑話奇談」(偏偏學堂時期的長安最害怕被當成笑話),小說點到輒止。京劇《金鎖記》卻著墨甚濃,七巧與長安的拉鋸,充以漫天猩紅的光,在長安淒厲的叫聲中,七巧唱著「要叫兒、足弓似月、步步難」,是上半場最為驚駭的衝突事件。劇作家巧妙渲染長安裹腳一段,寫出曹七巧「如此遭際何以堪」的積怨,也點出了長安活在母親激情之下,「如此遭際何以堪」的相同詰問。劇作家不忘「鳳紋耳墜子」,當初令七巧春心搖漾傾羨的耳畔軟語,如今卻連皮帶肉被親生女兒拉扯下去,鳳紋耳墜子再怎麼美,終究只是掛在曹七巧生命裡的蝨子。劇作家照應甚密,據此設計戲劇高潮,情緒充分架疊,滿懷忿怒的七巧覷著長安的臉,看見了令她幾十年來「步步難」的骨癆丈夫,直把過往的魂魅再種到了女兒的身上,待到宿怨的根發芽,長安走起路來、說起話都與平生所恨的母親無異了。
京劇《金鎖記》增設婚筵抽煙一景,曹七巧對長白與芝壽的喜慶視若無睹,沉浸在鴉片帶來的麻痺中,讓兒女跟著一起抽兩筒,減了痛苦,身體的或心理的,卻上了癮。京劇以煙霧蒸騰,多聲伴唱建立恍惚迷離之感,以「霧濛濛、氣氤氳」的唱詞委婉寫意,實際卻有更重要的指涉——「飛揚、墜沉、天高、淵深、風輕、水重、逍遙、羈籠」短短十六字,卻是本劇舉重若輕的命題。以吸煙為引,道出那些曾以為的飛揚、天高不過只是沉淪的開始,所輕信的逍遙風輕,卻是厚重的羈絆,曹七巧的一念,換來的卻是紅顏金銀兩相誤,窒息的金鎖。短短十六字,極為精彩。
京劇《金鎖記》運用大面藍、紅光,堆疊出冷峻、血腥的森森鬼氣,舞臺從姜家大院垂幕上富貴毛氈花紋式樣,到二房空無一物的闃寂四壁,只有一道重重深門,不知通往何處,門叩中央的橘黃圓形與另一矮櫃造型相仿,卻宛若套頸枷鎖——「此身早是無所有,唯有這黃金枷鎖重沉沉」。分家時,曹七巧鬧騰了一番,以為「多少年的恨、多少年的怒,到如今也只有這樣的償還」,緩緩步向深門,好似逃離了腐膩氣息的姜家,卻沒想到仍舊「過上了殘廢的氣」,到底逃不了。隨後,芝壽于歸再入重門,諷刺的是外頭懸搭著囍字聯,裡邊坐著的卻是等著曹七巧剃刀般的妒恨與怨毒摧花折莖的可憐少女。「他不是她母親的兒女,他決不能徹底明白她母親的為人。」小說裡長安提防著世舫認識她的母親,她知道母親的能耐,可芝壽呢?京劇《金鎖記》讓芝壽又再度走進舞臺深門,芝壽象徵性地解脫了,逃離名存實亡的姜家媳婦,逃離了七巧。曹七巧卻再也沒出過那扇門,直到羅漢床上抱恨終老。終於能明白張愛玲筆下「多年前的鬼」、魏海敏叨念著的「死人」,都是揮之不散的、假假真真的記憶牽纏,毛骨悚然。
京劇也頻繁運用切割、蒙太奇【2】的手法,兩相對照,王安祈說:「兩場婚禮,兩場麻將,映照出的是虛實、真假、正變、悲喜的變化,敘事結構如『照花前後鏡』般的參差對照。」【3】而我在技術與表演之間,看到了情感變化的暗示與類喻,例如三奶奶替長安向七巧說媒時,右側那廂是長安於一寸見方中側耳細聽,左側那廂是七巧與三奶奶話語協商,兩廂以燈光切割,在七巧答應婚事後,燈光的邊界消融,好似七巧與長安之間的某些傷痕被縫合,意料之外的是七巧嫉毀之心再起,燈光再次切割,母女依舊遙隔,燈光設計有意無意間,生發出饒富意蘊的聯想。此外,京劇又多次安排曹大年、曹大嫂等人以蒙太奇拼貼出七巧心理意識的喧聲,這些人都是七巧腦海裡的「鬼」,無法祛除的鬼,反覆重現。
小說尾聲在曹七巧晚年匆匆回溯了「喜歡她」的那些男人——「如果她挑中了他們之中的一個」。京劇《金鎖記》則選擇以「對門中藥鋪小劉」的三次登場,在在提醒曹七巧走到這一步都是自己的選擇,懟不得人,不過,若有那麼一刻七巧忘了自己是七巧,而只是選擇愛情,高唱「正月裡梅花粉又白」的少女,所有的哀與恨會不會有所不同?首尾相應的虛境彷彿在為曹七巧圓夢,或說源夢,這夢源於三十年以前的月,只可惜「碧樓朱櫳」的姜家堂錯付一個骨癆丈夫,這夢自然遠了,卻成為代代相傳的魘,籠罩著長白與長安。
從小說到戲曲,誠如劇作家趙雪君所言:「『事件』有敘述、『事件』能夠被解釋,但事件沒有聲音、沒有表情、沒有氣壓。」【4】京劇《金鎖記》確實做到小說文類無法提供的獨特的形容、狀態與氛圍,對讀小說,發現以曹七巧為視野的戲曲得以縱深其心靈,雖不及(或永不能及)張愛玲文字的「美麗與蒼涼」,卻體現了戲曲本質上的抒情性,並發揮戲曲的敘事特色,精要擇選片段,連綴而成曹七巧的舞臺生命簡影——「真長,這寂寂的一剎那」。
註釋:
1、王安祈曾以范鈞宏《春草闖堂》為例,提出「點線結構」:「『線』是戲劇情節的推演前進,『點』是霎那情感的停頓、醞蓄、誇張、深掘。『點線結構』原用來分析整齣戲的布局,⋯⋯當情節快速緊湊的推行至最緊張的時刻,編劇突然『凝結著時空』,以唱把此刻的情緒作淋漓盡致的抒發,觀眾的目光焦距仍維持在春草身上,情節的高潮得以持續延宕而不致一閃即逝。」(王安祈:〈演員劇場向編劇中心的過渡——大陸戲曲改革效應與當代戲曲質性轉變之觀察〉,《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十九期,2001年9月,頁278)
2、「蒙太奇」雖是電影術語,中國學者陳多亦曾提出「戲曲蒙太奇」的概念:「(戲曲藝術)不但在『場』與『場』的銜接上採用了『轉場戲的形式』;就是在一場戲、一小段戲中,也時常不斷靈活改變觀察劇中人的時間、空間、距離、角度。由於這些實踐的積累與豐富,戲曲就不僅是使用了『內心視象鏡頭』,還必然地有畫面的剪輯與組合的『蒙太奇』藝術手段。」(陳多:《陳多戲曲美學論——由媒介論看戲曲美的構成》,臺北:國家出版社,2006年,頁294)
3、藝術總監、編劇王安祈語,見節目單,頁9。
4、編劇趙雪君語,見節目單,頁12。
《金鎖記》
演出|國光劇團
時間|2022/04/03 14:30
地點|臺灣戲曲中心大表演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