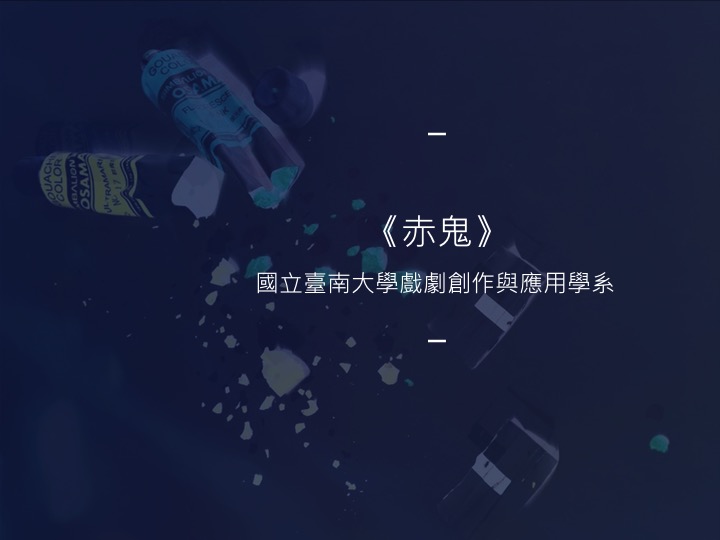
吳依屏(專案評論人)
《赤鬼》劇中的女主角曾發出這樣的疑問:「人怕鬼,因為鬼會吃人。但吃人的人又算什麼呢?吃人的人變成鬼了嗎?」針對這個有所隱喻的問題,《赤鬼》這齣戲試圖提供一個可供討論的空間。此劇利用晚著手點(late point of attack)的結構方式,埋下一個如同「海龜湯」般的謎題,引導觀眾跟隨劇中人物的口白,逐漸揭曉其中人物的種種經歷,以及最終女主角選擇從懸崖上跳水自殺的原因。
赤鬼的真實面目
這齣戲,名為赤鬼,呈現在觀眾眼前的,理所當然的是來路不明形容異常的「赤鬼」。而當觀眾聽到赤鬼發出的聲音原來是英文時,我們明白了所謂赤鬼指的是外人,或者該說是髮色、膚色甚至身形都不同於漁村人的外國人。有趣的是,當觀眾終於聽懂赤鬼說的語言是英文時,我們對於未知生物的恐懼害怕會瞬間消失,甚至對於劇中人的恐懼表現感到有種諷刺性的喜劇效果浮現。雖然劇中的赤鬼由於外貌的緣故而輕易被漁村居民排除驅逐,又由於語言不通的原因而使他的處境更為艱難;然而,這齣戲中的赤鬼與其說是這個仍維持善良、努力保護被母親丟下的嬰兒的鬼,倒不如說是恐懼異類的一般人心中的愚昧無知的具象化呈現。所以觀眾看到的反而是號稱是人類的種種缺點惡行:不斷說謊的騙子、說八卦造謠的婦女們、出爾反爾的居民、過於害怕而弄丟孩子卻又說謊的母親、以為吃掉赤鬼就能長生的愚昧老人等。
被驅逐的逐夢者
如果矇住雙眼而用心去體會、用耳朵去聽,我相信觀眾會發現:這些自稱為人而害怕被鬼吃的人類,心裡反而像是住著真正的惡鬼一般,小惡不斷,滋生惡意。甚至更為無奈的是,對劇中所謂的正常人而言,外人們都跟赤鬼一樣該被驅逐消滅。女主角/那女人——那個從外地搬來的女人——也被居民們排擠否定,她真正的名字從來沒有被表述過,而是用「妹妹」、「喂」、「那女人」來稱呼她。最後她與赤鬼開始溝通之後,她說自己的名字是「法克(fxck?)」,這個名字也令人啼笑皆非,既為劇中角色的處境感到無奈,也為所有不願屈服於傳統舊俗的女性感到悲涼。作為劇中同樣被標籤為外人,同樣追逐於自己夢想的人,女主角/妹妹與赤鬼/安格斯可說是同樣帶有某種固執天真色彩的追夢者。由於追逐夢想的動力驅使,赤鬼/安格斯來到這個陌生的海岸,而由於追逐夢想的緣故,女主角/妹妹再度帶領其他三人離開這個海岸。這種英雄主義的夢想追索導致死亡的選擇反而成為一種合情合理的結束方式。
台南大學戲劇系的《赤鬼》在舞台設計上獨具巧思,運用帶有滾輪的可拆卸道具,流暢通順地轉換場景。而演員們的表現也一樣可圈可點,值得讚美,特別是一人分飾多角的設定,極為考驗演員們的肢體語言及表情管理,但是四個演員皆極為自然的勾勒出諸多角色的形態樣貌,而不顯突兀。然而,瑕不掩瑜的則是音樂設計,在配樂的選擇及音效的播放方面常常有種怪異且格格不入的感覺,或許仍有斟酌修改的空間。
《赤鬼》是一齣意象豐富,帶有強烈道德思辨氛圍的戲劇。雖然背景建立於日本民間傳說,然而編劇野田秀樹所叩問的議題卻無關背景直擊人心,「何為人?何為鬼?」這個大哉問的答辯貫串全劇,看觀眾如何解讀。雖然劇中唯二的浪漫主義者/鬼最後都以死亡的方式悲劇收場,劇作家看似消極以對人性黑暗,然而我們必須理解,正如羅曼羅蘭所說:「世上只有一種真正的英雄主義,那就是在認識生活的真相後依然熱愛生活。」)(There is only one heroism in the world: to see the world as it is and to love it.)你說呢?
《赤鬼》
演出|國立臺南大學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
時間|2022/3/26 14:30
地點|臺南大學榮譽校區多功能實驗劇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