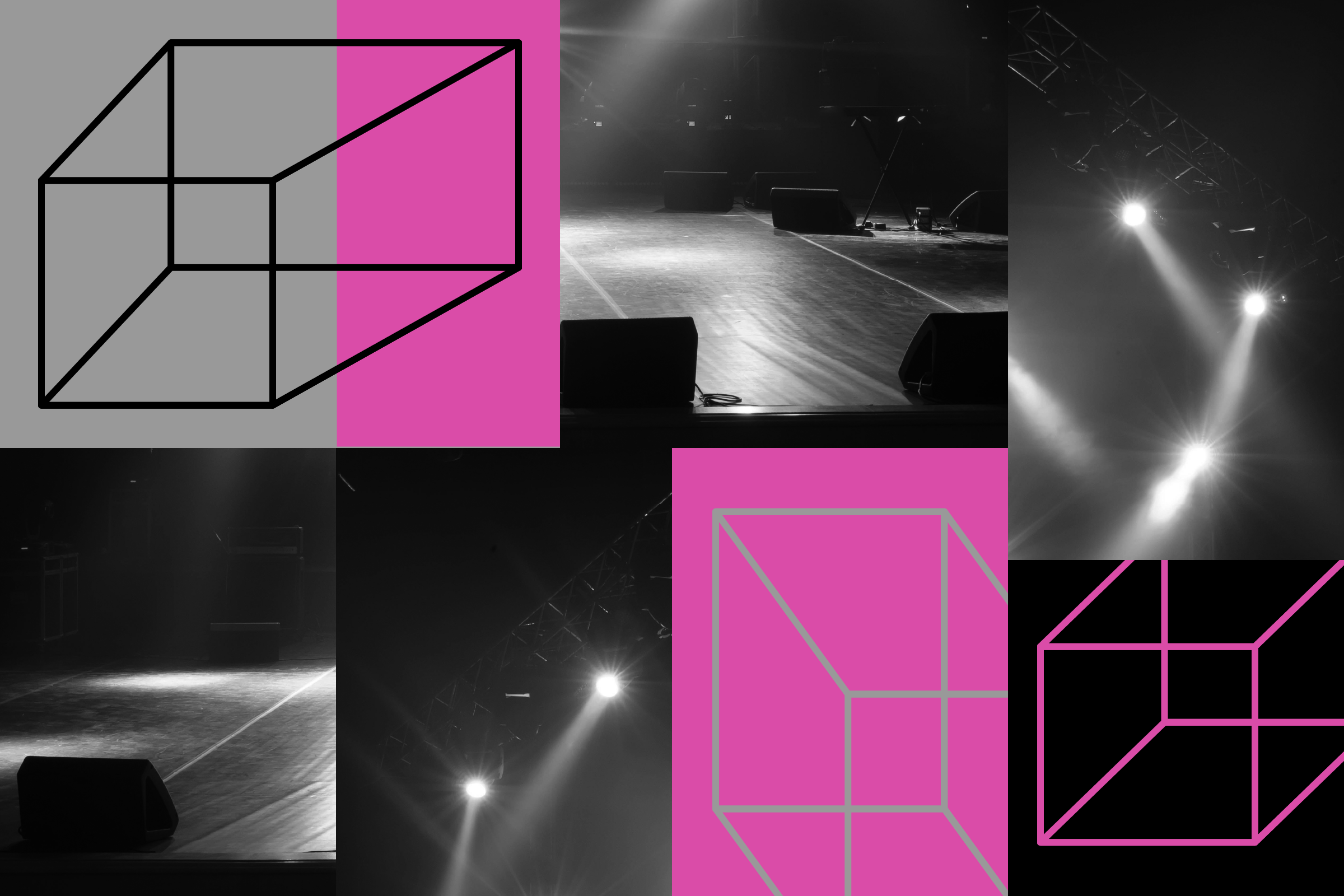
文 王嬿筑(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舞蹈系碩士)
雨過天晴的夜晚,我來到淡水雲門劇場。濕潤的草叢在月光下閃耀著晶瑩的光澤,空氣中瀰漫著木頭與濕土的氣息,大自然彷彿滲透進整個劇場,為觀眾帶來一場深度沉浸的感官體驗。
舞台潔白如紙,如同湖水反射清輝般的燈光,波光粼粼。沒有繽紛的色彩,也沒有澎湃的音樂,一切都極為純粹。舞台的簡約使觀眾的感官被放大,在昏暗朦朧的光影中,看不清舞者的樣貌,卻能感受到微微的呼吸,以及他們口中模擬出的蟬鳴、風聲與鳥叫。層層交疊的光影之間,依稀浮現舞者們蜷伏的身形。他們以四肢支撐身體,低頭背對觀眾,緩慢且有節奏地爬行。透過這樣的動作帶動背部肌肉,配合不同節奏的呼吸,使肌肉線條呈現出高低起伏的樣態,仿佛將看似靜止的大地因呼吸而充滿生機。
隨後,舞者們如雲瀑般層層覆蓋、堆疊與擴散,形塑出如山脈般的風景。這種編排方式宛如電影鏡頭,從一粒塵土逐漸拉遠至連綿山巒的全貌。此時,一位舞者緩緩站起,以手帶動軀幹,自在的穿行於身體周圍。他的軌跡如同登山時蜿蜒的山徑,引領觀眾隨之起伏流動。
燈光漸亮,如清晨的陽光透過樹葉灑落下來。舞者身穿膚色背心與米色長褲,身上點綴著淡淡的顏料。沒有具象的樹木、花朵等裝飾,他們如同詩行,自由地在舞台上以舞蹈書寫登山遊記。山林的白噪音持續響起,一位舞者豎立在如山脈般的群舞中,與獨舞者對立相望,他們以聲音呼喚彼此,在舞台上時而翻滾、時而繞圈,如兩隻老鷹於空中交會飛翔。古琴般的旋律在劇場中回盪,節奏簡約,質樸中透著禪意。燈光聚焦於獨舞者身上,他雙腕相扣,動作輕柔而優雅,彷彿於月光下綻放的一朵花,一瓣一瓣,緩慢地開展。
進入舞作尾聲,燈光漸暗,夜色低垂。舞者口中發出低沉的「嗡——嗡——」聲,如同寂靜中耳際泛起的共振。他們以跪姿散落在舞台上,靜止不動,山林的寧靜如山水畫般映現在觀者眼中。最後,舞者們如雲霧般緩緩消散,各自以不同的方式離開舞台。燈光最終歸於全黑,唯有蟲鳴與鳥叫聲,仍在劇場中悠悠迴盪。
在舞作中有許多節奏上的空拍、舞蹈動作的靜止和舞台空間的留白,這種編排手法讓整個作品更富韻味,也為觀眾留下一片想像的空間。當表演結束,劇場重歸寧靜,那些未說出口的語言、未舞出的情感,卻仍在心中緩緩迴盪,如同餘音裊裊,不散的山林之氣。
《定光》
演出|雲門舞集
時間|2025/04/10 20:00
地點|雲門劇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