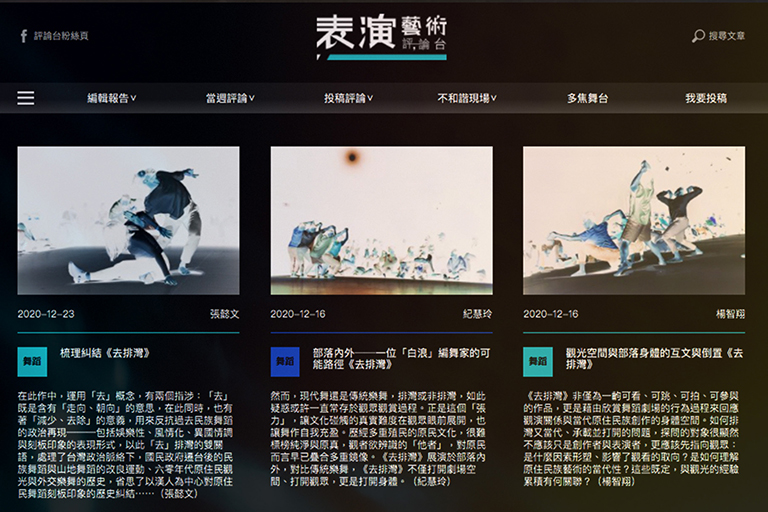
莊國鑫(編舞家)
【編輯報告:關於Reread】
因應疫情期間劇場關閉,以及表演藝術節目暫停或取消之變局,評論台擬以專題重新審視過往評論,思考相關議題,作為沉潛與積累之助力,同時冀許評論的作用與價值重新被召喚與正視。
此專題「Reread:再批評」,意為評論的評論。邀請評論人就近期較引起熱議的評論文,重新加以分析、討論。Reread也意在讓評論回到「文本」,增強它作為「生產者/作品」的面向,藉此,一方面呼應評論可供議論的公共性價值,並同步檢驗目前台灣評論文章的質素、差異、認同。
為延伸討論風氣與力道,再批評文章刊出後,歡迎被評論人或其它評論人予以回應或回饋,也歡迎讀者投稿,共襄討論。
———往下滑,開始閱讀莊國鑫【Reread:再批評】回應《去排灣》與陳盈帆——向內凝視的我族觀點———
筆者並未觀賞《去排灣》,但讀了多篇《去排灣》評論文章以及陳盈帆再次評論文,不知怎地,腦海總浮現臺灣舉辦「全國原住民運動會」傳統樂舞蹈比賽項目之畫面。這個於1999年開始、每兩年舉辦一次的全國性原住民運動賽事,源自更早前的「全省原住民運動會」,而多年下來,比賽項目方面每屆並不固定,多採原住民擅長的奧運和亞運競賽項目,也含原住民傳統競技項目,如傳統樂舞、鋸木、狩獵、擲茅等【1】。在傳統祭儀與舞蹈比賽項目上,(以我參加的是1995年的競技項目)為了所謂的評審公正、公平、專業性,評審身分幾乎希望皆具有原住民族身分,以維持並避免非原住民評審觀點的價值/歧義介入,而影響此一競賽之公正性。只是,這樣的安排並未能顧及臺灣多元原住民族群樂舞的相異性與獨特性,以至於不同的族群的部份樂舞的表現,呈現上總是無法獲得較理想的成績。
在「我」作為原住民相對「非原住民的他者」,「我族」內的樂舞呈現或比賽已是如此涇渭分明,回到《去排灣》,薪摩爾古薪舞集舞蹈總監巴魯・瑪迪霖(Baru Madiljin)在《去排灣》所強調的四步舞,以傳統性而言,也正是強調其在排灣族內部與排灣族樂舞的正統性,但此傳統經由他族觀視或參與創作,勢必產生不同解讀與運用,正如評論人未必了解「四步舞」內涵,觀視如同旁觀,甚至某種窺視,於短促的展演時間內。就筆者觀看Youtube上《去排灣》影片,一股無法言語形容的原住民自我內心的敏感騷動與尖刺,不免覺得此一「去」的意念是否多餘!因身處當代,巴魯已無法脫離成長背景中被殖民化的宿命,誠如法農(Frantz Omar Fanon)所言:「去殖民所面對的最嚴峻的挑戰,並不是歐洲殖民者的船堅炮利、商品貨幣或宗教信仰,而是被殖民者在有意識、無意識間,不斷仿效、複製殖民『母國』的一切結構,成為了她擺脫不了的母體。」【2】傳統舞蹈必須靠近某些既定印象,《去排灣》必須去除印象,架接四步舞與現代舞,當身為原住民編舞者終究擺脫不了汲汲地追尋、探索所謂「當代」原住民樂舞的文化緊箍咒,卻忘了反身思索,傳統進入當代難道就不成為「當代」原住民樂舞嗎,如何再移用、架接另一種「當代」而成為當代,其中的自覺與不自覺是否如法農所言?
因此,他者(編舞家林文中)的介入僅只能成為《去排灣》形變之催化劑,而四步舞本身真正的質變,需端看巴魯與藝術總監路之・瑪迪霖(Ljuzem Madiljin)如何凝視排灣文化,再從創作、發表中探索、檢討與發現,才能讓自己的藝術生命發光發熱,並達成自己對族群文化的承諾與貢獻。
巴魯心中追尋「我是誰?」、「我該如何跳?」及「觀者要看我們跳什麼?」三者間做了相當大程度的深刻讓渡與權宜,意即想跳脫觀者的凝視角度來進入舞作的核心,卻又不斷的探問「我是誰?」、「我該如何跳?」無窮盡的自我輪迴討論中,但此乃他者(連同為原住民、阿美族的我)都無法涉入的。也因此,我們若僅以動作、歌謠、肢體、形態、表徵、動機一一去檢視《去排灣》的創作動念,事實上遠不足以碰觸其內心之萬一。
而生存於主流社會體系下的舞者的身分認同,自然也無法逃脫大環境之影響。就蒂摩爾古薪舞集四位舞者長時間浸透於部落氛圍下的劇場,從實際生活、工作於部落的情境下,想見其應然壯大了其主體性,逐漸藉由肢體為一載體,可以承載《去排灣》的種種呈現模式,不因舞者的族裔身分相異性而有所區別。所以,我們可以看見的是從編舞者之創作轉至舞者身上時,亦有一段「我族/他族」的移轉過程,其過程是削弱或增強原有主體性,應該也是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焦點。
註釋
1、參考臺灣棒球運動館網頁,「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歷年資料,瀏覽時間:2021/6/23
2、法農,《大地上的受苦者》,楊碧川譯。臺北市:心靈工坊文化,2009。
《去排灣》
演出|
時間|
地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