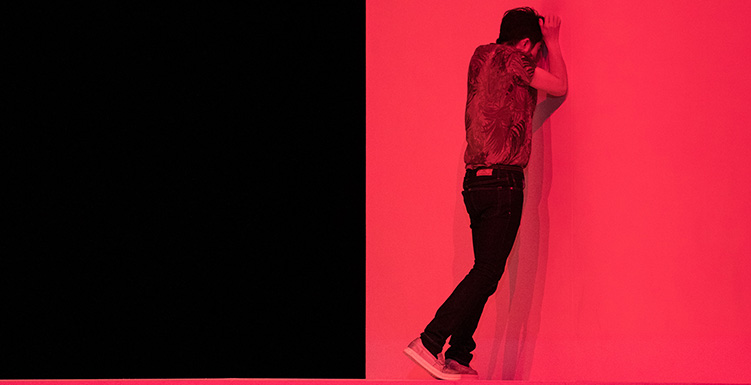
共同體的(不)可能
《馬密》選擇了非勝利式的凱旋歌,其關鍵所在當然是愛滋病的陰影。如同劇中受訪者所暗示:當同志不是問題,當一個有愛滋病的同志才是問題。換言之,在一片同志平權的大方出櫃歡呼聲中,「愛滋病」成了新的櫃子,區隔著「健康、快樂與愛家」的中產好同志以及「生病、陰鬱與縱慾」的敗德壞同志。疾病本身是中性的,而一個疾病能夠對主體認同產生如此大的影響,更多的是在社會話語建構下,與疾病產生聯想的性道德恐慌。【4】「愛滋病」做為二十世紀致命的性病,與不遵守單一性伴侶的「淫亂」男同志聯繫起來,成為區隔好與壞同志的指標。性學研究先驅Gayle Rubin在其1984年〈想想性〉(Thinking Sex)一文當中尖銳地指出,在「恐性」(sex negativity)的主流社會裡有一個性模式的位階,性模式與一夫一妻繁衍式的性愈靠近的位階愈高,愈趨向基督教神聖婚姻與愛情的高精神價值,因而被讚揚鼓勵;反之,愈是遠離這模式的,比如無繁衍功能的自慰,同性性交,多人性交,與物件的無人性交……位階愈低,被看成是靈魂墮落、道德淪喪的「獸性」行為,對於文明社會的維繫具有摧毀性力量。【5】如果如同劇作所說,《馬密》是一齣修補共同體的療癒之作,愛滋病陰影成了這個想像共同體的創傷原始場景,透過通俗劇裡常見的三角關係張力,劇作以三個主角的私人情感故事寓言了更大了同志想像共同體的形成、分裂與瓦解。劇作分別塑造出了三位面對愛滋病態度迥異的主角──縱慾無度的感染者甘口、嚴格維持健康形象的感染者馬密以及在兩者間搖擺的非感染者阿凱。換言之,三個角色分別代表的主體位置在某個程度上也輻射出台灣同志運動自九O年代以來產生的路線分裂以及內部立場矛盾。如果1994年何春蕤在反性騷擾大遊行中喊出「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的口號,引發婦女團體對性工作者的兩極化反應,由此開啟日後「國家女性主義」與「性解放」兩派在性別平權運動上的路線之爭,今天的「婚姻平權」與「毀家廢婚」派在同志運動的分歧是這個路線之爭的延續。由此來看,面對國家以及全球NGO介入台灣的在地愛滋病管理與同志社群性活動控制必然也產生非常不同的態度與批判路線。【6】在劇中共同體的分裂導因於馬密對警察告密甘口聚眾無套性愛,而引來國家機器介入這個情色烏托邦,進而引發三人不可縫合的關係破裂。馬密因而認為自己是「叛徒」,背棄了其原先相信的「同志」共同體,成為一個EX GAY,把自己重新交回上帝的眷顧,不再選擇同性戀的生活模式。
要了解主創對這段歷史過程的態度,我們必須回到作品本身的結構分析。到底主創對於三位主角所分別代表的位置透露出什麼樣不同的態度?姪女均凡不啻化身為劇作的敘事主體,她是歷史的後來者,以追索重建的方式試圖走入這個共同體的創傷記憶。重要的是這個敘事主體並不是全然客觀的旁觀者,她帶著處理自身創傷的目的回到歷史現場,那是一段混亂少女時期未婚生子而墮胎的痛苦回憶,她因為自身的創傷而在生命的軌道上與馬密相遇,就在警察破獲現場後不久,均凡赴叔叔的約,卻遇見了唯一沒有被帶走的馬密,兩人初次相見,馬密卻成了均凡生命重要的救贖者,他與她因為彼此的「陽性」狀態(一個愛滋同志,一個未婚懷孕)而相濡以沫。兩個人在Gayle Rubin的性位階上都是屬於被主流賤斥而出的邊緣人,就在馬密代替阿凱帶均凡去墮胎之前,他握著均凡的手,痛哭流涕對上帝說了一段關於善惡的祈願詞,接著便接到全劇的高潮片刻:均凡的墮胎儀式與趴場裸男集體被抓的影像疊加了起來。從戲劇結構來說,這高潮片刻的儀式寓言不言自明,墮胎與逮捕,一個直接殺生、一個間接殺人,從舞台的空間調度、視覺運用以及音樂設計上被合而為一,成為馬密變回馬泰翔,均凡擺脫未婚媽媽狀態的犧牲儀式。而在這個犧牲儀式之後,位階低的「愛滋男同」馬密得以昇華到位階高的「虔誠基督徒」馬泰翔;位階低的「未婚少女」均凡洗刷名譽,再生為位階較高的「自由獨立現代女性」。尤有甚者,馬密還留下了十萬塊保命錢給均凡,幫助她「重獲新生」。從這個敘事結構來說,《馬密》的確讓人不安,在重建歷史記憶的過程裡,創造了這兩個悲劇英雄腳色,形成一條觀演關係的同情認同線,而馬姊姊的原初創傷場景敘事如果有著關鍵位置,其以虔誠基督徒口吻進行的敘事更像是懺悔告解,她直說「我弟弟得病是我害的」,又說「歹路不能走」,弟弟的得病是縱容顧客在KTV包廂偷情的報應結果。馬密的背叛似乎是一條從肉慾墮落昇華至神的精神國度,重新「找到自己」的過程。這樣的情節開展似乎再度強化主流同運對「健康、快樂、愛家、守貞」的同志主體召喚?而「不知悔改」的甘口以及「立場搖擺」的阿凱終究要退出舞台中心,被掃入記憶的灰燼裡?回顧九O年代情慾噴井以及性少數運動的爆發,《馬密》是否終究走到了一條趨近新公民社會主流認同的道路,高舉新的十字架(如同演出時變成教堂的框中框舞台在肅穆的音樂下忽然拉進觀眾席,讓十字架的視覺突然高占全場),以新的犧牲安穩一個新的主體位置?
回憶錄的(不)可能
以上讓筆者不安的詮釋是否是創作者的立場?欲求進一步深化討論,接著我想回到一開頭關於紀錄劇場處裡真實的問題。《馬密》雖然「採訪了五個相關團體、十多位受訪者,包含帶原者及其伴侶、友人、社工、學者,並蒐羅閱讀了市面上所有關於愛滋的文字作品」【7】,但是整個演出還是落在「虛構事件」上,與道森列舉的案例不同,一般記錄劇場一定會在演出裡明顯指涉出社會裡發生的具體事件,即便其目的在於挑戰再現歷史事件真實性的可能與否。耿一偉其實也指出「紀錄劇場」發展到了當代,已經不再相信以重現真實事件進而達到政治變革的手法,更多的時候是「批判性的面對檔案」,打開「紀錄」與「紀實」之間再現政治的討論空間。【8】《馬密》以「可能的」回憶錄為標題,其實闡明了創作者面對歷史檔案的批判性開放態度,而選擇不以確切事件或人物為指涉座標點,應該也是為了避開對號入座的閱讀方式。【9】
就演出結構來說,「犧牲場景」之後,還接著均凡終於找到當下的馬密,在教堂與她重逢的場景,這是理解均凡面對三人矛盾態度的重要時刻,一方面均凡不停透過對話,要「失憶」的馬泰翔想起過去的馬密,在連番詰問後,馬泰翔終於說出了內心的秘密:他是叛徒,而他告密的起因更多是因為自身的忌妒與愛的無能,他坦白了自我內心的黑暗面;有趣的是均凡卻試圖說服他不是叛徒,她理解他內心的痛與無助,他的背叛是源自於自身情感的脆弱。在這裡《馬密》從同志作為一個政治化共同體的處理角度進入了個人處理愛、忌妒與孤寂的哲學性命題,也打開了〈想想性〉裡頭關於性模式位階的討論,試圖將性模式的選擇從公民性主體政治位階的討論拉回到個人祈求身心幸福所做的不同選擇,所以「叛徒」終究在均凡的同理下得到了原諒,一無反顧走向後同志的生命選擇。接著,均凡撥電話給阿凱叔叔,老去的他依舊守在甘口身邊,而「不知悔改」的甘口此時已然病重,值得慶幸的是阿凱以及一幫朋友持續站在他身邊直到最後一刻,準備與保險公司纏鬥。就這樣的安排來說,阿凱與甘口並沒有被掃入歷史灰燼,他們的情慾烏托邦持續到了當下,他們雖然身體「不貞」,但對彼此如此忠誠的情義,讓共同體走到了最後一刻。這是《馬密》在犧牲儀式後提出的兩面觀點,最後更以紀錄片的播放儀式,將受訪的諸人群聚到舞台現場,如果劇場表演歷史,注定是虛實難辨,此刻的我們彷彿聽見《哈姆雷特》裡的Horatio大喊:「今晚再度現身的這鬼影到底是誰?」無法忠實再現的過往,此刻以鬼影幢幢降臨現場。
劇本寫成後,由許哲彬導演,在2017年的兩廳院實驗劇場演出,後來因為反應熱烈,一片好評於水源劇場加演。【10】今年順勢成為兩廳院台灣國際藝術節(TIFA)的節目,進入大劇場演出。筆者有幸看過兩場演出,記憶所及,演職員沒有決定性更動(唯一明顯的差異是這次老去的阿凱由製作人演出);情節內容、導演手法與舞台設計亦相去不遠,最明顯的差別是在變大的舞台上加了一個移動的框中框舞台(最後轉身變成教堂,純白的設計,高懸的十字架跟往前推進的場面調度在這次觀賞經驗裡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所以,基本上兩次演出沒有結構手法上的關鍵性改變,還算是同一個作品。但是為何那在小劇場空間顯得如此得宜的虛實辯證、過去與當下交疊的美學技巧(透過投影與表演重建事件在空間上的並置交錯),放在大劇場以後竟然顯得尷尬而空虛?我們當然可以就技術面的場面調度、演員表演方式跟導演手法商議其「改善」之道,筆者不得不認為戲劇院的場地特質與作品本身有本質上的違和。
《馬密》作為一個質疑真實,挑戰記憶的作品,必然是屬於非主流展演空間的「小劇場」。而模仿歐洲歌劇院建築空間的戲劇院,其透視法的鏡框式空間結構,形成於歐洲新古典時期肖真原則(verisimilitude),以創造絕對幻覺為目的,服務於正在形成的歐洲現代民族國家想像共同體裡的中產階級市民群體。《馬密》讓妖孽進入廟堂,從文化生產的場域政治來說,不啻說明了台灣同志群體從邊緣進入主流公民論述的歷史過程,而如同本文以上所說,《馬密》以愛滋創傷為起點,以個人記憶折射歷史敘事,從「我」到「我們」之間試圖拉出一個想像共同體的政治命運寓言。然而其質疑真實建構的美學本質,必然讓這樣的共同體療癒目的枉然,如同劇末均凡在播放紀錄片時面對觀眾現身說法,此刻身為觀眾的我們,與舞台上再度回返的群鬼瞬間雙身一體,我們能看見的不過是破碎而片段的過往,人物之間過往的真實情感已經枉然、無法複製。
《馬密》試圖打破鏡框式舞台的幻覺,然而作為「國家」級的場館卻依舊堅固不摧,廟堂終究鎮住了妖孽,那些說話的幽靈被空間吞噬,在腦海裡留下的是那個不斷拉入前景的十字架,以及比現實人生更巨大的虛擬人像投影。在一個後現代去真實的時代,當擬像被放入現代國家神話的祭壇,虛構是否吞噬了真實血肉?
回憶錄到底可不可能?這問題關乎著國家劇院舞台上共同體的可不可能。《馬密》把妖孽帶進了廟堂,國家級的鏡框式舞台卻宛若無可遁形的照妖鏡,照出言人人殊的幢幢鬼影,也彰顯出現下台灣劇場處理創傷記憶、共同體療癒的可能與不可能。
註釋
4、關於疾病與社會道德建構的學術論述可以參考蘇桑‧桑塔格(Susan Sontag)著,程巍翻譯,《疾病的隱喻》,台北:麥田出版社,2012年。
5、請參考“Thinking Sex: Notes for a Radical Theory of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 in Abelove, H., Barale, M. A., and Halperin, D. M. eds., The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6、運動史的演變與路線之爭複雜而必須有更學術的文章進行梳理,不在本文討論的範疇,這邊羅列一些文獻供有興趣的人參考並推進討論:黃道明編,《愛滋治理與在地行動》,桃園: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2012年。何春蕤、甯應斌編,《性/別20》,桃園: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2016年。
7、謝謝黃道明的交流討論,並指出這篇評論。訊息從一篇原刊於2017年12月號《今藝術》的網誌得知,請見〈聆聽當下:《叛徒馬密可能的回憶錄》的同志再現〉,網址:https://tsaiyuchensa.blogspot.com/2017/12/blog-post.html?fbclid=IwAR15f4UH98XG1qklmKMfka9n9ZxwRAtuX2OI2ILGOCyT-r0TZGFNOyIEePk。
8、請參考耿一偉,〈在台灣思考紀錄劇場〉。
9、雖然如此,馬密的原型一再讓人聯想到「下一代幸福聯盟」高舉的「後同、前同運分子」韓森,請見其自我現身說法:https://taiwanfamily.com/2743。關於其所出版之《韓森的愛滋歲月》及其引發的愛滋治理邏輯與批判請見黃道明,〈國家道德主權與卑污芻狗:《韓森的愛滋歲月》裡的結社、哀悼與匿名政治〉,《愛滋治理與在地行動》,桃園: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2012年,頁1-55。
10、這次演出的評論諸多,請見表演藝術評論台跟台新藝術獎的ARTalks網站。
《叛徒馬密可能的回憶錄》
演出|四把椅子劇團
時間|2019/03/02 14:30
地點|國家戲劇院
